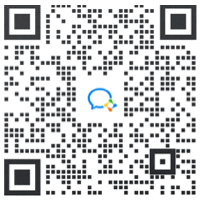目录
Content
进入一师附小
做过一次生意
转入新育小学
新育小学的校舍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看捆猪
看杀人
九月九庙会
看戏
学英文
国文竞赛
报考邮政局
考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船上生活
在西贡①
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大学(1946~1948)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眼前充满光明
陷入会议的漩涡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1950年至1956年的学术研究
政治环境
1978年
1979年
1981年
1983年
迎新怀旧
我疾病的早期历史
一进西苑医院
西苑二进宫
西苑三进宫
张衡插曲
艰苦挣扎
三〇一医院
奇迹的出现
病房里的日常生活
第三次大会诊
简短的评估
反躬自省
我感到惭愧
对未来的悬思
回家
三进宫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儿什么
难得糊涂
九三述怀
如何生活?
我不能封笔
进入一师附小
第二年,我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16年以后的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暗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总之是一点儿具体的影像也没有。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动也极潇洒。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可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做过一次生意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处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声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转入新育小学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原来,当时已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言为白话。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在帐篷里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1920年,我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小三班,少我一年。一字之差,我争取了一年。
新育小学的校舍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离我们家不算远。校内院子极大,空地很多。一进门,就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青草,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绿叶擎天的盛况,而今则是荒草凄迷、碎石满池了。
校门东向。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的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年龄比我们都大,国文水平比我们都高。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在家乡读过书以后,为了顺应潮流,博取一个新功名,便到济南来上小学。他们还带着厨子和听差,住在校内。令我忆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
进东门,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门上有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四个笔画繁多的字很好玩。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后,树木蓊郁。那里长着几棵树,能结出黄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从规模来看,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是否有纳兰词中所写的“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那样的荣华,不得而知,但是,极有气派,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也非词人,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任它荒凉衰败、垃圾成堆了。
花园对面,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没有多少房子,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里面隔成了许多间,被校长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会计、总务之类的部门,分别占据。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碳画像,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用“界画”的办法画成的。我觉得,并不很像。走下大屋的南台阶,距离不远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一团锦绣。出一个篱笆门,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
出高台阶的东门,就是“循规蹈矩”小径的尽头。向北走进一个门极大的院子,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间,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顶遮盖,下雨淋不着,走廊墙上是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走过两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个大操场,对一个小学来说,操场是够大的了。操场上有双杠之类的设施,但是,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几间房子,是教员住的,门前有一棵古槐,覆盖的面积极大,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我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人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当时的小学教员,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什么国文、数学(当时好像是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因为程度极浅,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一想到李老师,就想起了两件事。一件是,某一年初春的一天,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李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顺便说一句,当时西红柿还没有传入济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当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这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师辅导我们英文。认识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腰细。这个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记得课堂上的英文是怎样教的,但既然李老师辅导我们,则必然有这样一堂课无疑。好像还有一个英文补习班。
另一位教员是教珠算(打算盘)的,好像是姓孙,名字当然不知道了。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Shao qian,就是蝉,因此学生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Shao qian,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学生从来没有笑脸。打算盘本来是一个技术活,原理并不复杂,只要稍加讲解,就足够了,至于准确纯熟的问题,在运用中就可以解决。可是这一位Shao qian公,对初学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极残酷不合理的规定: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错到几十个到一百个数,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时老师打累了,才板下开恩。那时候体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来岁的孩子到哪里去告状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出来。
那时候,新育已经男女同学,还有缠着小脚去上学的女生,大家也不以为怪。大约在我高小二年级时,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女教师,年纪不大,教美术和音乐。我们班没有上过她的课,不知姓甚名谁。除了她新来时颇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之外,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至于职员,我们只认识一位,是管庶务的。我们当时都写大字,叫做写“仿”。仿纸由学生出钱,学校代买。这一位庶务,大概是多克扣了点儿钱,买的纸像大便用的手纸一样粗糙。山东把手纸叫草纸。学生们就把“草纸”的尊号赏给了这一位庶务先生。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育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在新育三年的记忆得特别清楚。一闭眼,一幅完整的新育图景就展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是昨天才离开那里似的,校舍和人物,以及我的学习和生活,巨细不遗,均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更奇怪的是,我上新育与上一师附小紧密相连,时间不过是几天的工夫,而后者则模糊成一团,几乎是什么也记不起来。其原因到现在我也无法解释。
新育三年,斑斓多彩。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对所有的正课,我都采取对付的办法。上课时,不是玩儿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柳成阴,秋天风卷落叶,冬天白雪皑皑。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可以为我写照。当时写作文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儿,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竟一辈子舞笔弄墨,逐渐体会到,写文章是要讲究结构的,而开头与结尾最难。这现象在古代大作家笔下经常可见。然而,到了今天,知道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已不多了。也许有人竟以为这是怪论,是迂腐之谈,我真欲无言了。有一次作文,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句子通顺,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可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悔。从那以后,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
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
我一生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新育小学时期,一点儿也不内向,而是外向得很。我喜欢打架,欺负人,也被人欺负。有一个男孩子,比我大几岁,个子比我高半头,总好欺负我。最初我有点怕他,他比我劲儿大。时间久了,我忍无可忍,同他干了一架。他个子高,打我的上身。我个子矮,打他的下身。后来搂抱住滚在双杠下面的沙土堆里,有时候他在上面,有时候我也在上面,没有决出胜负。上课铃响了,各回自己的教室,从此他再也不敢欺负我,天下太平了。
我却反过头来又欺负别的孩子。被我欺负得最厉害的是一个名叫刘志学的小学生,岁数可能比我小,个头差不多,但是懦弱无能,一眼被我看中,就欺负起他来。根据我的体会,小学生欺负人并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个人有劲使不出,无处发泄,便寻求发泄的对象了。刘志学就是我寻求的对象,于是便开始欺负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如果他鼓起勇气,抵抗一次,我也许就会停止,至少是会收敛一些。然而他是个窝囊废,一丝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这当然更增加了我的气焰,欺负的次数和力度都增加了。刘志学家同婶母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向家里告状,他父母便来我家告状。结果是我挨了婶母一阵数落,这一幕悲喜剧才告终。
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怎么会一下子转成内向了呢?这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母亲,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够想像的。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却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不给我做。在平常琐末的小事中,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对于这些事情并不敏感。但是,积之既久,在自己潜意识中难免留下些印记,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行动。我清晰地记得,向婶母张口要早点钱,在我竟成了难题。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都在院子里铺上席,躺在上面纳凉。我想到要早点钱,但不敢张口,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时间已接近深夜,才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要几个小制钱。钱拿到手,心中狂喜,立即躺下,进入黑甜乡,睡了一整夜。对一件事来说,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影响不大的。但是时间一长,性格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合情合理的。
看捆猪
新育小学的西邻是一个养猪场,规模大概相当大,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大概是屠宰业的规定,第二天早晨杀猪,头一天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就把猪捆好。但是
Content
进入一师附小
做过一次生意
转入新育小学
新育小学的校舍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看捆猪
看杀人
九月九庙会
看戏
学英文
国文竞赛
报考邮政局
考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船上生活
在西贡①
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大学(1946~1948)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眼前充满光明
陷入会议的漩涡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1950年至1956年的学术研究
政治环境
1978年
1979年
1981年
1983年
迎新怀旧
我疾病的早期历史
一进西苑医院
西苑二进宫
西苑三进宫
张衡插曲
艰苦挣扎
三〇一医院
奇迹的出现
病房里的日常生活
第三次大会诊
简短的评估
反躬自省
我感到惭愧
对未来的悬思
回家
三进宫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儿什么
难得糊涂
九三述怀
如何生活?
我不能封笔
进入一师附小
第二年,我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16年以后的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暗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总之是一点儿具体的影像也没有。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动也极潇洒。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可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做过一次生意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处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声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转入新育小学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原来,当时已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言为白话。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在帐篷里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1920年,我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小三班,少我一年。一字之差,我争取了一年。
新育小学的校舍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离我们家不算远。校内院子极大,空地很多。一进门,就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青草,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绿叶擎天的盛况,而今则是荒草凄迷、碎石满池了。
校门东向。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的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年龄比我们都大,国文水平比我们都高。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在家乡读过书以后,为了顺应潮流,博取一个新功名,便到济南来上小学。他们还带着厨子和听差,住在校内。令我忆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
进东门,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门上有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四个笔画繁多的字很好玩。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后,树木蓊郁。那里长着几棵树,能结出黄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从规模来看,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是否有纳兰词中所写的“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那样的荣华,不得而知,但是,极有气派,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也非词人,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任它荒凉衰败、垃圾成堆了。
花园对面,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没有多少房子,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里面隔成了许多间,被校长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会计、总务之类的部门,分别占据。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碳画像,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用“界画”的办法画成的。我觉得,并不很像。走下大屋的南台阶,距离不远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一团锦绣。出一个篱笆门,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
出高台阶的东门,就是“循规蹈矩”小径的尽头。向北走进一个门极大的院子,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间,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顶遮盖,下雨淋不着,走廊墙上是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走过两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个大操场,对一个小学来说,操场是够大的了。操场上有双杠之类的设施,但是,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几间房子,是教员住的,门前有一棵古槐,覆盖的面积极大,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我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人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当时的小学教员,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什么国文、数学(当时好像是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因为程度极浅,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一想到李老师,就想起了两件事。一件是,某一年初春的一天,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李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顺便说一句,当时西红柿还没有传入济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当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这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师辅导我们英文。认识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腰细。这个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记得课堂上的英文是怎样教的,但既然李老师辅导我们,则必然有这样一堂课无疑。好像还有一个英文补习班。
另一位教员是教珠算(打算盘)的,好像是姓孙,名字当然不知道了。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Shao qian,就是蝉,因此学生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Shao qian,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学生从来没有笑脸。打算盘本来是一个技术活,原理并不复杂,只要稍加讲解,就足够了,至于准确纯熟的问题,在运用中就可以解决。可是这一位Shao qian公,对初学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极残酷不合理的规定: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错到几十个到一百个数,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时老师打累了,才板下开恩。那时候体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来岁的孩子到哪里去告状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出来。
那时候,新育已经男女同学,还有缠着小脚去上学的女生,大家也不以为怪。大约在我高小二年级时,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女教师,年纪不大,教美术和音乐。我们班没有上过她的课,不知姓甚名谁。除了她新来时颇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之外,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至于职员,我们只认识一位,是管庶务的。我们当时都写大字,叫做写“仿”。仿纸由学生出钱,学校代买。这一位庶务,大概是多克扣了点儿钱,买的纸像大便用的手纸一样粗糙。山东把手纸叫草纸。学生们就把“草纸”的尊号赏给了这一位庶务先生。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育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在新育三年的记忆得特别清楚。一闭眼,一幅完整的新育图景就展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是昨天才离开那里似的,校舍和人物,以及我的学习和生活,巨细不遗,均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更奇怪的是,我上新育与上一师附小紧密相连,时间不过是几天的工夫,而后者则模糊成一团,几乎是什么也记不起来。其原因到现在我也无法解释。
新育三年,斑斓多彩。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对所有的正课,我都采取对付的办法。上课时,不是玩儿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柳成阴,秋天风卷落叶,冬天白雪皑皑。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可以为我写照。当时写作文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儿,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竟一辈子舞笔弄墨,逐渐体会到,写文章是要讲究结构的,而开头与结尾最难。这现象在古代大作家笔下经常可见。然而,到了今天,知道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已不多了。也许有人竟以为这是怪论,是迂腐之谈,我真欲无言了。有一次作文,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句子通顺,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可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悔。从那以后,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
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
我一生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新育小学时期,一点儿也不内向,而是外向得很。我喜欢打架,欺负人,也被人欺负。有一个男孩子,比我大几岁,个子比我高半头,总好欺负我。最初我有点怕他,他比我劲儿大。时间久了,我忍无可忍,同他干了一架。他个子高,打我的上身。我个子矮,打他的下身。后来搂抱住滚在双杠下面的沙土堆里,有时候他在上面,有时候我也在上面,没有决出胜负。上课铃响了,各回自己的教室,从此他再也不敢欺负我,天下太平了。
我却反过头来又欺负别的孩子。被我欺负得最厉害的是一个名叫刘志学的小学生,岁数可能比我小,个头差不多,但是懦弱无能,一眼被我看中,就欺负起他来。根据我的体会,小学生欺负人并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个人有劲使不出,无处发泄,便寻求发泄的对象了。刘志学就是我寻求的对象,于是便开始欺负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如果他鼓起勇气,抵抗一次,我也许就会停止,至少是会收敛一些。然而他是个窝囊废,一丝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这当然更增加了我的气焰,欺负的次数和力度都增加了。刘志学家同婶母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向家里告状,他父母便来我家告状。结果是我挨了婶母一阵数落,这一幕悲喜剧才告终。
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怎么会一下子转成内向了呢?这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母亲,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够想像的。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却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不给我做。在平常琐末的小事中,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对于这些事情并不敏感。但是,积之既久,在自己潜意识中难免留下些印记,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行动。我清晰地记得,向婶母张口要早点钱,在我竟成了难题。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都在院子里铺上席,躺在上面纳凉。我想到要早点钱,但不敢张口,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时间已接近深夜,才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要几个小制钱。钱拿到手,心中狂喜,立即躺下,进入黑甜乡,睡了一整夜。对一件事来说,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影响不大的。但是时间一长,性格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合情合理的。
看捆猪
新育小学的西邻是一个养猪场,规模大概相当大,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大概是屠宰业的规定,第二天早晨杀猪,头一天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就把猪捆好。但是
看了又看
暂无推荐
验证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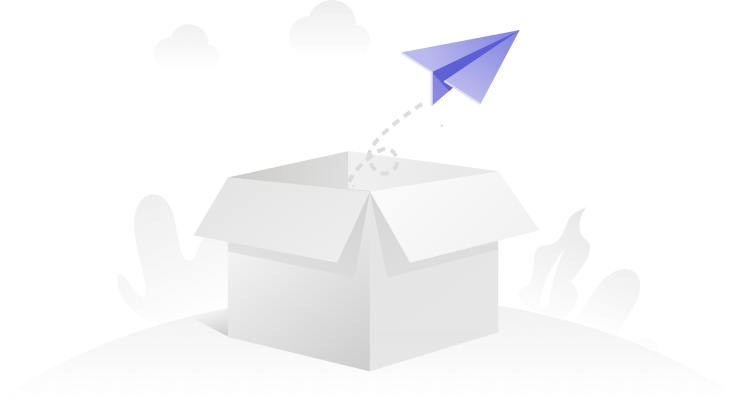
目前该文件尚无匹配的数据质量验证程序。我们将在后续版本中提供相应的验证支持,敬请谅解。

季羡林自传
660.06KB
申请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