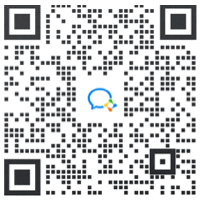目录
Content
序言
“人口激增”(1)
“人口激增”(2)
“人口激增”(3)
乡村重现生机
扰乱乡村
圈占森林
一个更为稳固的工匠阶层
采矿业的繁荣
副作用
金钱的重要性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铸币的恢复(1)
铸币的恢复(2)
“货币墙”
商业
富人的轮廓
分崩离析的社会
力量的新界限
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
小人物的末路
失败
劳工问题(1)
劳工问题(2)
走向“近代”国家
组织军事力量(1)
组织军事力量(2)
接下来是钱(1)
接下来是钱(2)
国家的经济
新老国王(1)
新老国王(2)
新老国王(3)
一个国王,一个国家
帝国主义在行进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1)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2)
序言
对世间万物的信仰与喜爱,兼具浪漫与理性的哲学引导基督徒从地狱走向天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神曲》中的伯纳德(Bernard)、贝亚特里切(Beatrice)和维吉尔(virago)引导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在14世纪初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呐喊比后人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能代表这个世界的苦闷,这个世界已走到了尽头,但它还要面对人们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阴霾、恐惧和灾难。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和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要面对毁灭、饥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体系对此无能为力。从圣路易(Salt Louis)到宗教改革爆发的这三个世纪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晚期处于衰退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更喜欢称之为“困难时期”,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这一时期很难界定,因而那些称呼不可避免地就有些模棱两可。中世纪何时结束?有什么标志性事件?是政治事件,如标志古代遗迹最后消失的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当时被人们低估,后来却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在未知的大西洋上的航行?还是1517年路德为公开反抗传统基督教的陈腐组织而对教会发起的挑衅性行为的爆发?又或者是现代学者们提出至迟在1540年或1560年新大陆的发现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日益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应该小心处理。亨利五世生活在中世纪,亨利八世则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界定。除了被人们诋毁的10、11世纪以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时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能,为其扩张准备如此多的财富,为未来发展积聚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转折点,但不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但丁的后裔们走出欧洲,征服新的大陆。这一光环必将闪耀在欧洲的上空。在那里,人们在抛弃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同时正在打造征服之剑。阿尔汗布拉(Alhambra)、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m)、苏莱曼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的其他名字将被人们铭记,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欧洲世界。
“人口激增”(1)
1420年至1430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之前的章节里分析的所有腐朽的因素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于可以摧毁一种文明。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以及许久以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受到的。米什莱(Michelet)认识到14世纪潜藏的隐义,然而他只是众多健在的或故去的诋毁中世纪的“危机”和“衰落”的人之一。为何不在此停止,以圣女贞德遭受火刑的熊熊柴堆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直至很久以后这种情景才发生了改变,这是在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时代之后,当时拉伯雷和加尔文正四处云游,他们的思想哺育我们直到1530年或1540年:介于贞德和路德之间的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被视为旧世界的终结:百年战争的结束,拜占廷的崩溃,黑死病,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忽略了:多桅小帆船已经在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文艺复兴已然开始,近代国家已经建立。历史被武断地切割。但是,在过去15年多的时间里,对法国的区域经济、意大利艺术和思想、德意志精神和英国社会的研究取得的进展,已经使这一概念化为乌有。这一段历史确定无疑地属于中世纪。在1450年和1540年至1450年之间,基督教的欧洲焕发出与之前的衰落截然相反的活力,尽管确如近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至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欧洲已经恢复到了1300年或1320年的水平,那是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欧洲才能见到的情况。但正是这段令人厌恶和排斥的时期,奠定了近代欧洲的根基。
这个有些过分的评论,略带错愕,是一位伦理学家于1520年做出的,它针对的是一种舍其则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的根本现象:即人类寿命的缩减最终结束。在1420年之后尤其是1470年的档案中有大批材料已被发现,所以相当可靠的人口研究首次得以进行。当时肯定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和模糊的。
曾经肆虐加剧人口锐减的传染病逐渐退去。黑死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发生于1437年和1440年,偶尔的发作则持续至1465年。例如,斑疹伤寒的记录见于1470年到1560年南特地区的一系列瘟疫记录中,90年里的51年有病情记载。而另一方面,麻风病只不过是一段令人不快的回忆,它从未席卷全部人口。它的消失是由于肺结核的发作——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后者对社会非特权阶层威海更大——还有梅毒,这种病在法国和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在1498年至1525年之间的“意大利战役”中也是如此。与这些相比,黑死病的影响相形见绌。其杆菌的致命性并不因医护条件的改进(直到1600年后才有所发展)或民众免疫力的逐渐增强而减弱,是人们体质的增强遏制了它的影响。与这一胜利相比,瘟疫的失败成了次要的现象。人们足以抵御它的侵袭,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战争在这一时期起了什么作用呢?与瘟疫相比较,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不同时期和地点,由骑兵队或由雇佣兵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较以前不那么频繁了。波尔多的收复(1453年),意大利的洛迪(Lodi)和平(1454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战争的结束以及皇帝斐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在1470年左右予以支持的城市间协议的制定,与游荡在阿尔萨斯的雇佣兵或被消灭,或于1440年到1450年之间应召成为皇家军队一样,这些都积极的。但是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法国境内的战争大体上结束了,在路易十一挫败大公军队的蒙特利尔(Montlhéry)之战(1465年)和一百年以后的宗教战争之间,阿图瓦和勃艮第的争斗一直持续至1480年,而且在1488年,吸血鬼(écorcheurs,敲竹杠者)还结队游荡在诸如法兰西岛(?le-de-France)这样的乡下。在英格兰,内战爆发了;在德国,骑士们,即里特(Ritter,中世纪有贵族身份的骑士、武士、骑士团成员),在整个莱茵兰和中部德意志强行采用武装自卫权(Faustrecht,封建贵族动用武力的权力),即武力原则;意大利自1490年以后再一次惨遭战火蹂躏。尽管战争如同我们早先看到的,是贵族们地位衰败的结果,在贵族们被消灭之后,政治扩张在国王的名义下得以迅速恢复。
“人口激增”(2)
尽管农业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食物短缺的情况日益减少,但饥饿依旧在大约1465年袭击了波旁(Bourbon)王朝的领地,1481年和1492年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受到波及,在1522年和1525年之间阿尔萨斯和西德意志也未能幸免。这些粮食短缺的危害在于,虽然很少有人直接死于饥饿,但它们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总之,在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没能形成可以使出生率上升所需的相对安全的环境,而延缓了最终的复苏。
尽管我们的信息在这一基点上是不充足的,但这确实表明促进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逐渐增强。农业的复兴是(贵族)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需求瓦解的直接结果。农民能够通过改进农具和耕作方式获得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口粮,这就使他们如同11和12世纪那样,得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尽管在1427年佛罗伦萨的灾难中一些家庭的20个儿童中有15个,或11个中有6个,年龄很小就已夭折(鉴于这一灾难记录了“家庭的平均值”,这些结果不会出错),但富裕家庭儿童的存活率开始重新增加。在里昂,瘟疫前平均每个妇女有个子女,这一数据到1430年跌至,并在这一水平上保持稳定,到1480年又攀升至或。毫无疑问,食品供应的改善在这种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回归先前的“婚姻模式”对于人口的增长同样重要,在这种模式下女子很早就出嫁,这有利于提高出生率。但是根据1427年的相关记述,有74%的农村女子到这一年龄已经出嫁(这一比率在城市中仅为58%),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据此在1425年声称,米兰有20 000名年逾20的女子还未出嫁。1480年之后,婚配陪嫁(Monte delle Doti)——一项由佛罗伦萨发起为适合结婚的女子提供嫁妆的基金因为缺少顾客几乎被迫关门。就我们所知,在这种婚姻中男子往往年龄较大,但是到15世纪,年龄介于23和27岁的男子被视为合适的新郎,与此相比,在1320或1340年之前30多岁的新郎则是屡见不鲜的。
一个迄今尚未能被科学验证的决定性因素也应被考虑到:即女性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这是当时环境中的一个偶发现象,例如由于可以对分娩提供更好的照顾和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或者是因为一种我们无法分析的长期的生物性趋势,这一事实经过开展这样的人口调查得到了确认。尽管在1427年的托斯卡纳男子仍然远远多于女子,而到1455年至1470年,巴塞尔、纽伦堡、阿图瓦和低地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男女的平均比例为85至90个男子对110至115个女子。从道德或经济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婚姻市场上的女子已经饱和,使得女子结婚的年龄降得更低而且更早地开始家庭生活。
对于导致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些因素,我们能否量化或确定其时间?总体趋势的发展是缓慢的,而且相当多样化,但毕竟没有类似1347年至1350年的明显的中断。在某些地区,如上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法兰西岛,直到15世纪末,人口水平持续下降;而在其他地区,像奥弗涅(Auvergne)、勃艮第、里昂、埃塞克斯(Essex)、埃诺(Hainaut)以及郎格多克的部分地区,人口从1440年起激增。如果谁选取英格兰、诺曼底和埃诺的平均值,就可以声称人口是从1410年至1420年之前的负增长向情况最好的大约1420年至1440年重新正增长转变,每年的增长系数为—。真正的增长始于1450年至1460年之后,当时的增长系数已经稳定在—。1475年后,尽管科(Caux)和郎格多克的增长率分别是和,但每年的增长率稳定在和之间,这代表了人口在3或4代间翻了一番。不幸的是,十五世纪初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趋于停滞,大多数国家居民的数量只有1310年或1320年的3/4或4/5。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口激增”归结于生育显得名不副实,而且大约在1550年左右人口数量重新开始下降更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超出了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简略提及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现象的不确定性。
“人口激增”(3)
还应提及一个决定性的、不应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形势似乎很特别。当然,情况一向如此,14世纪的危机使它们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通货膨胀和衰退。每一次城市移民的大潮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片残迹,我已指出这种增长拉开了城市对农民残酷掠夺的序幕。一旦最紧迫的危险过去,城市的魅力就不会暗淡,因为在它们的高墙背后,失业者和逃亡者意外的发现他们受到欢迎,而且工作比起乡下来也许更为轻松。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1450年后,几乎各地的移民都如此之多,使得城市议会面临严重的容纳问题。人口的流动因突发因素改变方向:在巴黎,大约1480年或1500年,来自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31%)同塞纳?埃?瓦瑟(Seine et Oise)的两个先前富庶地区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29%)以及来自卢瓦尔河(Loire)南部(直到后来被驱逐,其构成了18%的巴黎移民)的移民形成了竞争。很难对这种人口涌入的数量作出估计,据推测,在1435年和1455年之间移民分别占兰斯(Rheims)和斯特拉斯堡人口的25%和35%。若干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城市因移民的涌入人口重新大幅度增加,如瓦纳(Vannes)、雷恩、塞莱斯塔(Sélestat)或科尔马(Colmar)。此外,诸如阿尔勒(Arles)或佩里格(Périgueux),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之,尽管人口的数字并不能真正证明根本性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在1500年,绝大多数城市拥有和1300年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人口,里尔、第戎(Dijon)和根特的情形既是如此。这种增长姗姗来迟,甚至比乡下来的还晚,而且在147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在这些新的压力下,城市社会的立场坚决了,他们抛弃了新来人口中无利可图的部分,把其分派到郊区或者特定的城区。为了获得公民准入权(droit de cité)——在普罗旺斯、中央高地(Massif Central)和莱茵河沿岸的城市特许给予的公民权——一个人必须谋取一些土地或获得一处拥有契约的住宅(acte d’habitation),即使波尔多,也被先后两次大批的移民涌入瓜分殆尽。那些没有获得这些资格的人被抛出了城市,如同在大约1460年或1470年的勃艮第公国发生的一样。在短期内采取过激措施的统治者,并不认为通过清除一个反叛城市中的居民然后强制性地以新居民加以代替,就可以获得支持,就如同法国—勃艮第战争期间在阿腊斯和列日发生的一样。
乡村重现生机
农业复兴的条件与人口复兴类似,并与之相联系,由于各种分歧和矛盾是如此之大,农业复兴的总体进展难以确定。首先,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乡村重现生机的意义:约1460年,康布西斯(Cambrésis)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是6公升(16 1/2蒲式耳),凯尔西(Quercy)在1473年的产量仍是微不足道或是可以被忽略的,两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奥佛涅和普罗旺斯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开始耕作它们荒弃的份地。其他地区,如1484年法国的许多大庄园,或1489年当约翰·劳斯(John Rouss)和其他人向国王亨利七世纷纷抱怨时,1498年的托斯卡纳——如果萨沃纳罗拉(S*onarola)可以相信的话,以及1500年的丹麦,人们仍在抱怨乡村并没有完全复苏。但是,这一复苏的各种技术条件是可以确定的。例如,凯尔西的情形已经表明赋税经常由集体确定(在1450年和1490之间占到了这一地区税收比例的80%之多),因此也代表了一个特定地区各个阶层的共同的努力。另一方面,谷物的价格在1470年之后稳定下来, 这就使农民未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种植更多的谷物。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人数众多的工人而使工资增长速度趋缓。在英格兰,工资水平甚至在1430年到1450年之间以及1470年到1490年分别下降了10%和15%之多,也许这也是城镇之间竞争的结果。
这种复苏在各个阶段的诸多结果在整体上也许是这样呈现的:在1440年和1475年之间,人们大量种植能经济性作物,尤其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经营亚麻、葡萄园、果园以及橄榄园。从1475到1520年人们开始在贫瘠土地上清除份地,但是直到1520年,在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才开始开垦早在十四世纪就被抛荒了的荒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20%的农地重归耕犁之下。
尽管谷物的价格在1460年或1470年后略微上涨了,但耕地并未升值。在英格兰或诺伊堡(Neufbourg)每亩可耕地的价格保持其在1420年至1425年的水平。造成这种价格停滞的原因很清楚:农民在逐利的过程中,尝试用其它作物追逐利润,而且从14世纪中期起,一种土地专业化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如果像在大约1450年的勃艮第一样,一个葡萄园的维护费用为20里弗尔而收益为45里弗尔,为什么要冒险去种小麦呢?把小片的耕地变成赚钱的葡萄园可能包括停止所有的生产。在大约1500年,即使是容克贵族地主也设法将葡萄移植到萨克森。将葡萄和橄榄或是葡萄和坚果树混种,现在仍是许多南欧国家的特色风景,在当时的确极为普及。
农业的另一方面——畜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的兴趣。肉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
Content
序言
“人口激增”(1)
“人口激增”(2)
“人口激增”(3)
乡村重现生机
扰乱乡村
圈占森林
一个更为稳固的工匠阶层
采矿业的繁荣
副作用
金钱的重要性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铸币的恢复(1)
铸币的恢复(2)
“货币墙”
商业
富人的轮廓
分崩离析的社会
力量的新界限
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
小人物的末路
失败
劳工问题(1)
劳工问题(2)
走向“近代”国家
组织军事力量(1)
组织军事力量(2)
接下来是钱(1)
接下来是钱(2)
国家的经济
新老国王(1)
新老国王(2)
新老国王(3)
一个国王,一个国家
帝国主义在行进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1)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2)
序言
对世间万物的信仰与喜爱,兼具浪漫与理性的哲学引导基督徒从地狱走向天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神曲》中的伯纳德(Bernard)、贝亚特里切(Beatrice)和维吉尔(virago)引导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在14世纪初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呐喊比后人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能代表这个世界的苦闷,这个世界已走到了尽头,但它还要面对人们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阴霾、恐惧和灾难。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和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要面对毁灭、饥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体系对此无能为力。从圣路易(Salt Louis)到宗教改革爆发的这三个世纪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晚期处于衰退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更喜欢称之为“困难时期”,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这一时期很难界定,因而那些称呼不可避免地就有些模棱两可。中世纪何时结束?有什么标志性事件?是政治事件,如标志古代遗迹最后消失的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当时被人们低估,后来却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在未知的大西洋上的航行?还是1517年路德为公开反抗传统基督教的陈腐组织而对教会发起的挑衅性行为的爆发?又或者是现代学者们提出至迟在1540年或1560年新大陆的发现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日益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应该小心处理。亨利五世生活在中世纪,亨利八世则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界定。除了被人们诋毁的10、11世纪以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时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能,为其扩张准备如此多的财富,为未来发展积聚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转折点,但不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但丁的后裔们走出欧洲,征服新的大陆。这一光环必将闪耀在欧洲的上空。在那里,人们在抛弃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同时正在打造征服之剑。阿尔汗布拉(Alhambra)、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m)、苏莱曼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的其他名字将被人们铭记,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欧洲世界。
“人口激增”(1)
1420年至1430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之前的章节里分析的所有腐朽的因素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于可以摧毁一种文明。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以及许久以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受到的。米什莱(Michelet)认识到14世纪潜藏的隐义,然而他只是众多健在的或故去的诋毁中世纪的“危机”和“衰落”的人之一。为何不在此停止,以圣女贞德遭受火刑的熊熊柴堆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直至很久以后这种情景才发生了改变,这是在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时代之后,当时拉伯雷和加尔文正四处云游,他们的思想哺育我们直到1530年或1540年:介于贞德和路德之间的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被视为旧世界的终结:百年战争的结束,拜占廷的崩溃,黑死病,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忽略了:多桅小帆船已经在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文艺复兴已然开始,近代国家已经建立。历史被武断地切割。但是,在过去15年多的时间里,对法国的区域经济、意大利艺术和思想、德意志精神和英国社会的研究取得的进展,已经使这一概念化为乌有。这一段历史确定无疑地属于中世纪。在1450年和1540年至1450年之间,基督教的欧洲焕发出与之前的衰落截然相反的活力,尽管确如近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至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欧洲已经恢复到了1300年或1320年的水平,那是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欧洲才能见到的情况。但正是这段令人厌恶和排斥的时期,奠定了近代欧洲的根基。
这个有些过分的评论,略带错愕,是一位伦理学家于1520年做出的,它针对的是一种舍其则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的根本现象:即人类寿命的缩减最终结束。在1420年之后尤其是1470年的档案中有大批材料已被发现,所以相当可靠的人口研究首次得以进行。当时肯定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和模糊的。
曾经肆虐加剧人口锐减的传染病逐渐退去。黑死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发生于1437年和1440年,偶尔的发作则持续至1465年。例如,斑疹伤寒的记录见于1470年到1560年南特地区的一系列瘟疫记录中,90年里的51年有病情记载。而另一方面,麻风病只不过是一段令人不快的回忆,它从未席卷全部人口。它的消失是由于肺结核的发作——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后者对社会非特权阶层威海更大——还有梅毒,这种病在法国和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在1498年至1525年之间的“意大利战役”中也是如此。与这些相比,黑死病的影响相形见绌。其杆菌的致命性并不因医护条件的改进(直到1600年后才有所发展)或民众免疫力的逐渐增强而减弱,是人们体质的增强遏制了它的影响。与这一胜利相比,瘟疫的失败成了次要的现象。人们足以抵御它的侵袭,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战争在这一时期起了什么作用呢?与瘟疫相比较,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不同时期和地点,由骑兵队或由雇佣兵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较以前不那么频繁了。波尔多的收复(1453年),意大利的洛迪(Lodi)和平(1454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战争的结束以及皇帝斐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在1470年左右予以支持的城市间协议的制定,与游荡在阿尔萨斯的雇佣兵或被消灭,或于1440年到1450年之间应召成为皇家军队一样,这些都积极的。但是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法国境内的战争大体上结束了,在路易十一挫败大公军队的蒙特利尔(Montlhéry)之战(1465年)和一百年以后的宗教战争之间,阿图瓦和勃艮第的争斗一直持续至1480年,而且在1488年,吸血鬼(écorcheurs,敲竹杠者)还结队游荡在诸如法兰西岛(?le-de-France)这样的乡下。在英格兰,内战爆发了;在德国,骑士们,即里特(Ritter,中世纪有贵族身份的骑士、武士、骑士团成员),在整个莱茵兰和中部德意志强行采用武装自卫权(Faustrecht,封建贵族动用武力的权力),即武力原则;意大利自1490年以后再一次惨遭战火蹂躏。尽管战争如同我们早先看到的,是贵族们地位衰败的结果,在贵族们被消灭之后,政治扩张在国王的名义下得以迅速恢复。
“人口激增”(2)
尽管农业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食物短缺的情况日益减少,但饥饿依旧在大约1465年袭击了波旁(Bourbon)王朝的领地,1481年和1492年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受到波及,在1522年和1525年之间阿尔萨斯和西德意志也未能幸免。这些粮食短缺的危害在于,虽然很少有人直接死于饥饿,但它们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总之,在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没能形成可以使出生率上升所需的相对安全的环境,而延缓了最终的复苏。
尽管我们的信息在这一基点上是不充足的,但这确实表明促进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逐渐增强。农业的复兴是(贵族)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需求瓦解的直接结果。农民能够通过改进农具和耕作方式获得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口粮,这就使他们如同11和12世纪那样,得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尽管在1427年佛罗伦萨的灾难中一些家庭的20个儿童中有15个,或11个中有6个,年龄很小就已夭折(鉴于这一灾难记录了“家庭的平均值”,这些结果不会出错),但富裕家庭儿童的存活率开始重新增加。在里昂,瘟疫前平均每个妇女有个子女,这一数据到1430年跌至,并在这一水平上保持稳定,到1480年又攀升至或。毫无疑问,食品供应的改善在这种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回归先前的“婚姻模式”对于人口的增长同样重要,在这种模式下女子很早就出嫁,这有利于提高出生率。但是根据1427年的相关记述,有74%的农村女子到这一年龄已经出嫁(这一比率在城市中仅为58%),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据此在1425年声称,米兰有20 000名年逾20的女子还未出嫁。1480年之后,婚配陪嫁(Monte delle Doti)——一项由佛罗伦萨发起为适合结婚的女子提供嫁妆的基金因为缺少顾客几乎被迫关门。就我们所知,在这种婚姻中男子往往年龄较大,但是到15世纪,年龄介于23和27岁的男子被视为合适的新郎,与此相比,在1320或1340年之前30多岁的新郎则是屡见不鲜的。
一个迄今尚未能被科学验证的决定性因素也应被考虑到:即女性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这是当时环境中的一个偶发现象,例如由于可以对分娩提供更好的照顾和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或者是因为一种我们无法分析的长期的生物性趋势,这一事实经过开展这样的人口调查得到了确认。尽管在1427年的托斯卡纳男子仍然远远多于女子,而到1455年至1470年,巴塞尔、纽伦堡、阿图瓦和低地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男女的平均比例为85至90个男子对110至115个女子。从道德或经济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婚姻市场上的女子已经饱和,使得女子结婚的年龄降得更低而且更早地开始家庭生活。
对于导致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些因素,我们能否量化或确定其时间?总体趋势的发展是缓慢的,而且相当多样化,但毕竟没有类似1347年至1350年的明显的中断。在某些地区,如上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法兰西岛,直到15世纪末,人口水平持续下降;而在其他地区,像奥弗涅(Auvergne)、勃艮第、里昂、埃塞克斯(Essex)、埃诺(Hainaut)以及郎格多克的部分地区,人口从1440年起激增。如果谁选取英格兰、诺曼底和埃诺的平均值,就可以声称人口是从1410年至1420年之前的负增长向情况最好的大约1420年至1440年重新正增长转变,每年的增长系数为—。真正的增长始于1450年至1460年之后,当时的增长系数已经稳定在—。1475年后,尽管科(Caux)和郎格多克的增长率分别是和,但每年的增长率稳定在和之间,这代表了人口在3或4代间翻了一番。不幸的是,十五世纪初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趋于停滞,大多数国家居民的数量只有1310年或1320年的3/4或4/5。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口激增”归结于生育显得名不副实,而且大约在1550年左右人口数量重新开始下降更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超出了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简略提及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现象的不确定性。
“人口激增”(3)
还应提及一个决定性的、不应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形势似乎很特别。当然,情况一向如此,14世纪的危机使它们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通货膨胀和衰退。每一次城市移民的大潮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片残迹,我已指出这种增长拉开了城市对农民残酷掠夺的序幕。一旦最紧迫的危险过去,城市的魅力就不会暗淡,因为在它们的高墙背后,失业者和逃亡者意外的发现他们受到欢迎,而且工作比起乡下来也许更为轻松。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1450年后,几乎各地的移民都如此之多,使得城市议会面临严重的容纳问题。人口的流动因突发因素改变方向:在巴黎,大约1480年或1500年,来自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31%)同塞纳?埃?瓦瑟(Seine et Oise)的两个先前富庶地区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29%)以及来自卢瓦尔河(Loire)南部(直到后来被驱逐,其构成了18%的巴黎移民)的移民形成了竞争。很难对这种人口涌入的数量作出估计,据推测,在1435年和1455年之间移民分别占兰斯(Rheims)和斯特拉斯堡人口的25%和35%。若干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城市因移民的涌入人口重新大幅度增加,如瓦纳(Vannes)、雷恩、塞莱斯塔(Sélestat)或科尔马(Colmar)。此外,诸如阿尔勒(Arles)或佩里格(Périgueux),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之,尽管人口的数字并不能真正证明根本性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在1500年,绝大多数城市拥有和1300年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人口,里尔、第戎(Dijon)和根特的情形既是如此。这种增长姗姗来迟,甚至比乡下来的还晚,而且在147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在这些新的压力下,城市社会的立场坚决了,他们抛弃了新来人口中无利可图的部分,把其分派到郊区或者特定的城区。为了获得公民准入权(droit de cité)——在普罗旺斯、中央高地(Massif Central)和莱茵河沿岸的城市特许给予的公民权——一个人必须谋取一些土地或获得一处拥有契约的住宅(acte d’habitation),即使波尔多,也被先后两次大批的移民涌入瓜分殆尽。那些没有获得这些资格的人被抛出了城市,如同在大约1460年或1470年的勃艮第公国发生的一样。在短期内采取过激措施的统治者,并不认为通过清除一个反叛城市中的居民然后强制性地以新居民加以代替,就可以获得支持,就如同法国—勃艮第战争期间在阿腊斯和列日发生的一样。
乡村重现生机
农业复兴的条件与人口复兴类似,并与之相联系,由于各种分歧和矛盾是如此之大,农业复兴的总体进展难以确定。首先,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乡村重现生机的意义:约1460年,康布西斯(Cambrésis)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是6公升(16 1/2蒲式耳),凯尔西(Quercy)在1473年的产量仍是微不足道或是可以被忽略的,两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奥佛涅和普罗旺斯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开始耕作它们荒弃的份地。其他地区,如1484年法国的许多大庄园,或1489年当约翰·劳斯(John Rouss)和其他人向国王亨利七世纷纷抱怨时,1498年的托斯卡纳——如果萨沃纳罗拉(S*onarola)可以相信的话,以及1500年的丹麦,人们仍在抱怨乡村并没有完全复苏。但是,这一复苏的各种技术条件是可以确定的。例如,凯尔西的情形已经表明赋税经常由集体确定(在1450年和1490之间占到了这一地区税收比例的80%之多),因此也代表了一个特定地区各个阶层的共同的努力。另一方面,谷物的价格在1470年之后稳定下来, 这就使农民未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种植更多的谷物。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人数众多的工人而使工资增长速度趋缓。在英格兰,工资水平甚至在1430年到1450年之间以及1470年到1490年分别下降了10%和15%之多,也许这也是城镇之间竞争的结果。
这种复苏在各个阶段的诸多结果在整体上也许是这样呈现的:在1440年和1475年之间,人们大量种植能经济性作物,尤其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经营亚麻、葡萄园、果园以及橄榄园。从1475到1520年人们开始在贫瘠土地上清除份地,但是直到1520年,在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才开始开垦早在十四世纪就被抛荒了的荒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20%的农地重归耕犁之下。
尽管谷物的价格在1460年或1470年后略微上涨了,但耕地并未升值。在英格兰或诺伊堡(Neufbourg)每亩可耕地的价格保持其在1420年至1425年的水平。造成这种价格停滞的原因很清楚:农民在逐利的过程中,尝试用其它作物追逐利润,而且从14世纪中期起,一种土地专业化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如果像在大约1450年的勃艮第一样,一个葡萄园的维护费用为20里弗尔而收益为45里弗尔,为什么要冒险去种小麦呢?把小片的耕地变成赚钱的葡萄园可能包括停止所有的生产。在大约1500年,即使是容克贵族地主也设法将葡萄移植到萨克森。将葡萄和橄榄或是葡萄和坚果树混种,现在仍是许多南欧国家的特色风景,在当时的确极为普及。
农业的另一方面——畜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的兴趣。肉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
看了又看
暂无推荐
验证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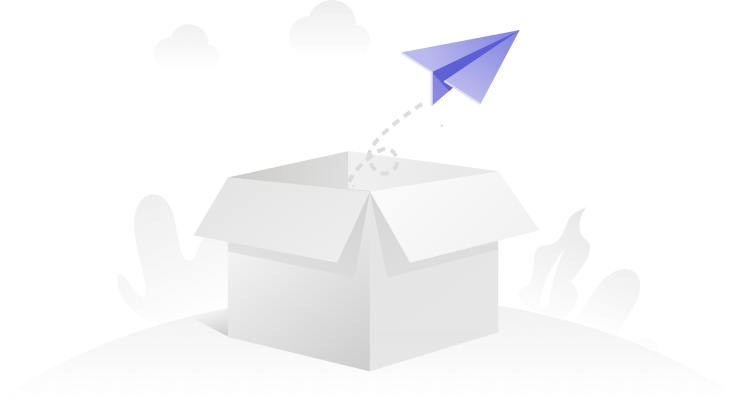
目前该文件尚无匹配的数据质量验证程序。我们将在后续版本中提供相应的验证支持,敬请谅解。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491.7KB
申请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