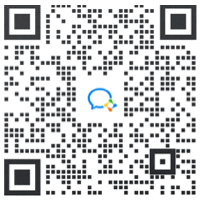目录
Content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一节
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执业于加州的私人侦探。我现年三十二岁,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前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事儿让我寝食难安。我为人友善,朋友成群。我的公寓虽然狭小,可我喜欢这种局促的空间。我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拖车式活动房里;但这段时间以来,我渐渐觉得它们太精致了,不太合我的口味。所以我选择了住单间,做一个“单身女人”。我不养宠物,也不爱养花种草。我就喜欢成天到处跑跑,做些分内之事。除了职业本身的危险性之外,我的生活一直很普通、平稳,而且充实。杀人这种事让我觉得怪怪的,我一时间无法理清思绪。我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供述,每一页供词上都有我的首字母签名,最后还签上了我的全名。我还写了一份同样的报告,作为文书存档之用。这两份文件叙述的都是客观事实,措词拐弯抹角,并没有把事实完全交代清楚……
尼基·法伊夫第一次来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三周以前的事了。我曾经为加州信实保险公司工作过,所以在该公司庞大的办公室套间中,我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和这家公司的关系比较松散。我为他们开展某些调查业务;作为交换,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单独门户的两个小房间和一个俯瞰着圣特雷萨主大街的小阳台。我订了电话应答服务,当我外出时有人会替我接电话。我还自己做账;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能保持收支平衡。
那天的整个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办事。当时我只是顺便回办公室取一下相机,却看见尼基·法伊夫站在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如果不是八年前她因为谋杀亲夫劳伦斯——本城赫赫有名的离婚案律师——而被判有罪时我正好在法庭的话,我可能根本不认识她。那时的尼基还未满三十岁,一头惹眼的淡金色头发,黑色的眼睛,皮肤好得无可挑剔。可能是由于监狱里的食物富含淀粉吧,她瘦削的面庞现在变得饱满一些了,但依然透着一种优雅轻灵之气。即使在被定罪的时候,这种气质也令谋杀指控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此时,她的头发已经恢复了本来的色泽,那是一种淡得近于无色的浅褐色。此时的她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吧。尽管如此,加州女子管教所的岁月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起初我一言未发,只是把门打开让她进去。
“你认识我。”她说。
“我曾经为你的丈夫办过几次事。”
她仔细审视着我,“仅此而已吗?”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你出庭受审的时候,我也在法庭上,”我说,“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否和你的前夫有什么私人瓜葛的话,答案是没有。我并无冒犯之意,但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要咖啡吗?”
她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已不再拘束。我从档案柜底层取出咖啡壶,又从门后拿出一瓶晶露,往咖啡壶注满水。她没有因为我如此费事而表示异议,这一点让我很赞赏。我放进一张滤纸,把咖啡磨成粉末,又将水壶接上电源。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和鱼缸中气泵发出的声音一个样,让人觉得十分安逸。
尼基静静地坐着,仿佛体里的情感部件已经脱节了。她没有那种惴惴不安的矫揉造作,没有吸烟,也没有摆弄自己的头发。我坐进自己的转椅里。
“你是什么时候出狱的?”
“一周以前。”
“自由的感觉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我想,感觉还不错吧,但没有自由我也能活下去,我过得比你想象中要好。”
我从自己右侧的小冰箱中抽出一个混装乳制品的小纸盒。我一般都把干净的杯子倒着放。我为我们俩翻起两只杯子,待咖啡煮好之后,倒上满满两杯。尼基端起杯,含糊地说了声谢谢。
“或许你以前也听过这种说法,”她继续说道,“但我真的没有杀劳伦斯;而且我想请你查清是谁杀了他。”
“为什么你要等那么长时间?你在狱中就可以启动调查的,那样可能还会让你省去不少牢狱之苦呢。”
她微微一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谁又相信我了?从我被指控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不再信任我。现在,我要把这份信任夺回来。而且我还要弄清楚,是谁陷害了我。”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现在我才发现它们是金属般的灰色。她表情冷静、情绪平和,似乎心中的火焰已经暗淡下去了。她看上去是一位没有多少幻想的淑女。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罪,可我已经想不起我如此固执己见的原因了。她看起来是个没有多少激情的人。我相信,她对任何事物的关心程度都不可能促使她去杀人。
“想跟我说说情况吗?”
她呷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到我的桌子边上。
“我和劳伦斯结婚四年多一点吧。婚后才六个月,他就背叛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深受打击。实际上,我也是这样跟他搅和在一起的……那时,他还没有离开他的第一个老婆。他背叛了?,和我在一起。我想,也许是当情妇可以带来某种自我满足感吧!但我从没想过会步她的后尘,这让我非常恼火。”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这就是你杀他的动机。”
“你也知道,他们要找个顶罪的人,那就是我,”她说到这儿终于显出了一丝激动,“过去这八年里,我和形形色色的杀人犯生活在一起。相信我,冷漠是不会成为动机的。你会因仇恨杀人,或者在盛怒下杀人,或者为了报复杀人,但你不会去杀你漠不关心的人。在劳伦斯死之前,我对他根本就无所谓了。从发现另一个女人的那一刻起,我对他的爱就消失了。我只花了一点点时间,就把这份爱从我心中抹去了……”
“你在日记里记的就是这些吗?”我问道。
第二节
“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在意。我仔细记下了每一次背叛。我偷听他的电话,还跟踪他在城里转悠。后来,他开始对所有事情都小心起来。我也慢慢失去了兴趣,后来就根本无所谓了。”
两片红晕爬上了她的脸颊。我没有说话,给她时间让她平静一下。“我知道,看起来好像是我因为嫉妒或者愤怒而杀了他,但事实上我已经对这件事彻底不在乎了。在他死前,我就打算要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回学校读书,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各走各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那你认为是谁杀了他?”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想杀他。他们具体干没干,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说,我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但是我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就是我到你这儿来的原因。”
“为什么会找到我呢?”
她的脸再次微微泛红。“我到城里的两家大事务所去问了一下,他们都回绝了我。我在劳伦斯以前的罗拉代克斯名片夹中偶然发现了你的名字。我想,我要请个他曾经雇过的人,似乎颇有讽刺的味道。我在谋杀组的康·多兰那里认真了解过你的情况。”
我皱起眉头说:“这个案子就是他办的,不是吗?”
尼基点了点头。“是他办的。他说你的记忆力很好。我可不愿意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讲个没完没了的。”
“多兰怎么看?他认为你是无辜的吗?”
“我想不会。但话又说回来,我已经服完刑了,那还关他什么事?”
我审视了她片刻。她很坦率,说得也在理。劳伦斯·法伊夫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家伙。我也一直不怎么喜欢他。如果她是有罪的,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旧事重提。除了还要渡过剩余的假释期之外,她的苦难已经结束了,她与社会之间所谓的债务已经一笔勾销。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我今天晚点儿会跟你联系的,到时再答复你。”
“非常感谢。我有的是钱,花多少都无所谓。”
“法伊夫太太,重新调查以前的案子我是不会收取报酬的。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即使我们查出了谁是真凶,要想定案也相当困难。我想查阅一下过去的档案,看看情况再说。”
她从她的大皮包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档案袋。“我搜集了一些剪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把这些都留给你。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纤小、冰凉,但很有力。“请叫我尼基。”
“我会跟你联系的。”我说。
因为一个保险索赔的案子,我需要出门给一条人行道上的裂缝拍照片。在她走后,我也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驾着我的大众轿车驶上了高速公路。我喜欢让自己的车里塞满东西。这辆车上就塞满了各种文件、法律书籍以及一只公文包。包里装着我的小型自动手枪、纸盒子,还有一名客户给我的一盒机油。他被两名诈骗高手骗走了两千美元,说是帮他投资到他们所谓的石油公司中。那盒机油倒是真的,但并不是他们生产的;他们在西尔斯30W型机油上贴了新标签。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逮到这两个家伙。除了这堆垃圾之外,我还在车上塞进了一只收拾妥当的过夜行李箱,天晓得是为了防备什么不时之需。我一般不愿为那些要求我仓促行动的人提供服务;但随身带着一套睡衣、牙刷和干净的内衣,总能让我觉得安心。我想我可能有些怪癖吧。我的大众车是六八年的车型,浅米色,带有各式各样的凹痕。车的发动机早就需要检修了,可我一直没时间。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起了尼基。我已经把装满剪报的马尼拉纸档案袋扔到了汽车后座上。事实上我根本不必看这些材料。劳伦斯·法伊夫办过很多离婚案,他声名远扬,号称“法庭杀手”。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不择手段,会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优势。加州和其他许多州一样,在这里,离婚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夫妻矛盾不可调和;二是精神失常无法治愈。以前,离婚案律师和私家侦探的惯用伎俩是靠捏造通奸来提出指控,不过现在这条路行不通了。但是,财产分配和监护权——也就是金钱和孩子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劳伦斯·法伊夫能够为他的客户——绝大多数是女人——夺得这一切。在法庭之外,他同样臭名远扬,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杀手”。据说在诉讼期间,判决与最后宣判之间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曾经抚慰过无数破碎的心。
我早就发现他人狡诈,几乎没有什么幽默感,可他做人严谨,为他做事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总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还提前支付报酬。但是,很多人都非常憎恨他:他夺走了男人们的财产,又辜负了女人们的信任。他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尼基当时厄运缠身:她受到了指控、遭到了审判并被认定有罪。除了那些明显涉及杀人狂的案子之外,警方总倾向于认为谋杀罪行是由我们所知或所爱的人犯下的,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居然是正确的。当你和一家五口人坐在一起共进晚?的时候,想想这些互相递送餐盘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凶犯,这真让人不寒而栗。
第三节
如果我记得没错,在劳伦斯·法伊夫被杀当晚,他曾经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查理·斯科索尼在一起喝酒。尼基则参加了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一次聚会。她先回到家中,而劳伦斯直至午夜才回家。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接受多种过敏症的治疗。在上床之前,他吞服了日常服用的胶囊,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醒了。他恶心、呕吐,并因剧烈的胃痉挛而蜷成一团。清晨来临时,他死了。尸检和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表明,他的死因是由于吃下了被磨成粉末并放置在他所服胶囊中替代了原有药末的夹竹桃。这种伎俩并不算很高明,但的确奏效。夹竹桃在加州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灌木;事实上在法伊夫家的后院里就长着一棵。在药瓶上除了他本人的指纹之外,还发现了尼基的指纹。在她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的一些条目详细记载了她已掌握丈夫与他人通奸的事实,还记下了她深受伤害、恼怒异常,并正在考虑离婚。地方检察官非常明确地认定,要想和劳伦斯·法伊夫离婚而不承担不利后果是不可能的。他以前结过婚,又离过婚。尽管他的离婚案是由另一位律师处理的,但他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并设法在财产分配中占尽了好处。加利福尼亚州在财产分配上是很严谨的,但劳伦斯·法伊夫在金钱调配方面颇有手段;即便是五五分成,他仍然能够分到大头。看起来尼基·法伊夫似乎对此相当清楚:与其通过法律手段和丈夫脱离关系,还不如采取其他措施。
她有作案的动机,也有作案的机会。大陪审团听取了证词,提交了起诉书。她一旦出庭,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哪一方能够说服十二位公民陪审员呢?很明显,地方检察官是有备而来的。尼基聘请了来自洛杉矶的法律天才——号称“必败官司之保护神”的威尔弗雷德·布伦特耐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乎等于承认她自己有罪了。整个审判都笼罩在一种哗众取宠的氛围之中。尼基年轻漂亮,出身富贵人家。这是个小城,公众又很好奇。这场好戏是不会被错过的。
圣特雷萨位于南加利福尼亚,是一座拥有八万人口的小城。它恰好坐落于太平洋与马德雷山脉之间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是落魄富人的一处避风良港。城里的公共建筑看起来就像陈旧的西班牙式教堂,而私人住宅则像杂志中的插图一样。棕榈树上那些难看的棕色叶片被修剪掉了;在蓝灰色山冈的背景下,洁白的小船在阳光下的水中荡漾,这一切让海滨广场风景如画,完美无瑕。城内中心区大多是两到三层的建筑,白色的墙、红色的瓦,线条柔和而开阔,还带有爬满了绚丽的褐红色九重葛的棚架。即便是那些贫民居住的木结构平房也不会让人觉得邋遢。
警察局坐落于接近小城中心的一条偏僻街道上。道旁是一排粉刷成薄荷绿色的小别墅;屋墙矮矮的,蓝花楹树上垂挂着淡紫色的花朵。南加利福尼亚没有秋天,火灾便是冬天的信使。冬天常常是阴云遮蔽;火灾的季节一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泥石流。此后天气便会好转。一切又周而复始,恢复正常,就像现在五月的天气一样。
我顺路将胶卷送去冲洗,随后就来到谋杀组找多兰中尉。康·多兰已经年近六十,不修边幅:眼睛下挂着眼袋、灰色的胡楂或是胡楂般的东西、松弛臃肿的脸颊;头发梳得掠过发亮的秃顶,并抹着一层不知名的男士护发品。一眼看去,他就像是个满身雷鸟酒味、整天在桥下闲游浪荡、吐得自己满鞋污秽的家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够精明。康·多兰比一般的盗贼要聪明得多。他与杀人犯们也难分高低;大多数时候,他都能逮到他们,偶尔才会弄错一回。很少有人能骗过他,不过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只不过是工作时非常专注,记忆力好而且做事十分冷静罢了。他早知道我的来意,一言不发地示意我跟他一起走进办公室。
康·多兰所谓的办公室,在任何其他地方只配给秘书用。他不喜欢与众人隔离开来,也不在乎所谓的私人空间。他喜欢靠在向后倾的椅子里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又对周围的工作状况有所关注。他用这种方式掌握了很多信息,因而不必再靠与下属交谈来了解情况。他知道手下的探员何时回来、何时外出,也知道都有谁被抓进来审问。他还知道报告未能及时写好以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他问道,语调中没有任何要帮忙的意思。
“我想看看劳伦斯·法伊夫的档案。”
他朝着我轻轻扬起一条眉毛,说:“这不符合警局的规定。我们这儿可不是公共图书馆。”
“我又没要求把它们拿走。我只是想看一下。你以前也让我这样看过的。”
“一次而已。”
“你心里清楚,我给你提供消息可不止一次了,”我说,“这次怎么又不爽快了?”
“那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那你更用不着反对了。这根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隐私。”
他脸上带着迟钝而严肃的笑容,懒洋洋地轻轻磕着一枝铅笔。我想,他可能在享受着冷冰冰地回绝我的权力。“是她杀的,金西。整个案子就是这样。”
“是你让她跟我联系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怀疑的话,为什么还要找麻烦呢?”
“我的怀疑与劳伦斯·法伊夫无关。”他说。
“那还有什么?”
“这件案子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他语焉不详地说,“或许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既得利益。”
“‘我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
“哦,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知道多少秘密。”他说。
第四节
“我也一样,”我说,“我们何必在这儿兜圈子呢?”
他露出一丝恼怒的神情,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情感。他不是个容易被看穿的人。“你知道我对你们这类人的看法。”
“瞧,就我来说,我和你干的是同一行,”我说,“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你对其他私人侦探有什么意见,但我一直没有碍过你的事;而且我对你的工作只有尊重,别无其他。我不明白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好好合作呢?”
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紧绷的嘴角泄气地松弛下来。“你要是学会调情的话,会从我这里套出更多东西来的。”他勉
Content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一节
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执业于加州的私人侦探。我现年三十二岁,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前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事儿让我寝食难安。我为人友善,朋友成群。我的公寓虽然狭小,可我喜欢这种局促的空间。我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拖车式活动房里;但这段时间以来,我渐渐觉得它们太精致了,不太合我的口味。所以我选择了住单间,做一个“单身女人”。我不养宠物,也不爱养花种草。我就喜欢成天到处跑跑,做些分内之事。除了职业本身的危险性之外,我的生活一直很普通、平稳,而且充实。杀人这种事让我觉得怪怪的,我一时间无法理清思绪。我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供述,每一页供词上都有我的首字母签名,最后还签上了我的全名。我还写了一份同样的报告,作为文书存档之用。这两份文件叙述的都是客观事实,措词拐弯抹角,并没有把事实完全交代清楚……
尼基·法伊夫第一次来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三周以前的事了。我曾经为加州信实保险公司工作过,所以在该公司庞大的办公室套间中,我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和这家公司的关系比较松散。我为他们开展某些调查业务;作为交换,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单独门户的两个小房间和一个俯瞰着圣特雷萨主大街的小阳台。我订了电话应答服务,当我外出时有人会替我接电话。我还自己做账;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能保持收支平衡。
那天的整个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办事。当时我只是顺便回办公室取一下相机,却看见尼基·法伊夫站在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如果不是八年前她因为谋杀亲夫劳伦斯——本城赫赫有名的离婚案律师——而被判有罪时我正好在法庭的话,我可能根本不认识她。那时的尼基还未满三十岁,一头惹眼的淡金色头发,黑色的眼睛,皮肤好得无可挑剔。可能是由于监狱里的食物富含淀粉吧,她瘦削的面庞现在变得饱满一些了,但依然透着一种优雅轻灵之气。即使在被定罪的时候,这种气质也令谋杀指控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此时,她的头发已经恢复了本来的色泽,那是一种淡得近于无色的浅褐色。此时的她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吧。尽管如此,加州女子管教所的岁月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起初我一言未发,只是把门打开让她进去。
“你认识我。”她说。
“我曾经为你的丈夫办过几次事。”
她仔细审视着我,“仅此而已吗?”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你出庭受审的时候,我也在法庭上,”我说,“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否和你的前夫有什么私人瓜葛的话,答案是没有。我并无冒犯之意,但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要咖啡吗?”
她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已不再拘束。我从档案柜底层取出咖啡壶,又从门后拿出一瓶晶露,往咖啡壶注满水。她没有因为我如此费事而表示异议,这一点让我很赞赏。我放进一张滤纸,把咖啡磨成粉末,又将水壶接上电源。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和鱼缸中气泵发出的声音一个样,让人觉得十分安逸。
尼基静静地坐着,仿佛体里的情感部件已经脱节了。她没有那种惴惴不安的矫揉造作,没有吸烟,也没有摆弄自己的头发。我坐进自己的转椅里。
“你是什么时候出狱的?”
“一周以前。”
“自由的感觉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我想,感觉还不错吧,但没有自由我也能活下去,我过得比你想象中要好。”
我从自己右侧的小冰箱中抽出一个混装乳制品的小纸盒。我一般都把干净的杯子倒着放。我为我们俩翻起两只杯子,待咖啡煮好之后,倒上满满两杯。尼基端起杯,含糊地说了声谢谢。
“或许你以前也听过这种说法,”她继续说道,“但我真的没有杀劳伦斯;而且我想请你查清是谁杀了他。”
“为什么你要等那么长时间?你在狱中就可以启动调查的,那样可能还会让你省去不少牢狱之苦呢。”
她微微一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谁又相信我了?从我被指控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不再信任我。现在,我要把这份信任夺回来。而且我还要弄清楚,是谁陷害了我。”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现在我才发现它们是金属般的灰色。她表情冷静、情绪平和,似乎心中的火焰已经暗淡下去了。她看上去是一位没有多少幻想的淑女。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罪,可我已经想不起我如此固执己见的原因了。她看起来是个没有多少激情的人。我相信,她对任何事物的关心程度都不可能促使她去杀人。
“想跟我说说情况吗?”
她呷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到我的桌子边上。
“我和劳伦斯结婚四年多一点吧。婚后才六个月,他就背叛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深受打击。实际上,我也是这样跟他搅和在一起的……那时,他还没有离开他的第一个老婆。他背叛了?,和我在一起。我想,也许是当情妇可以带来某种自我满足感吧!但我从没想过会步她的后尘,这让我非常恼火。”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这就是你杀他的动机。”
“你也知道,他们要找个顶罪的人,那就是我,”她说到这儿终于显出了一丝激动,“过去这八年里,我和形形色色的杀人犯生活在一起。相信我,冷漠是不会成为动机的。你会因仇恨杀人,或者在盛怒下杀人,或者为了报复杀人,但你不会去杀你漠不关心的人。在劳伦斯死之前,我对他根本就无所谓了。从发现另一个女人的那一刻起,我对他的爱就消失了。我只花了一点点时间,就把这份爱从我心中抹去了……”
“你在日记里记的就是这些吗?”我问道。
第二节
“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在意。我仔细记下了每一次背叛。我偷听他的电话,还跟踪他在城里转悠。后来,他开始对所有事情都小心起来。我也慢慢失去了兴趣,后来就根本无所谓了。”
两片红晕爬上了她的脸颊。我没有说话,给她时间让她平静一下。“我知道,看起来好像是我因为嫉妒或者愤怒而杀了他,但事实上我已经对这件事彻底不在乎了。在他死前,我就打算要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回学校读书,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各走各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那你认为是谁杀了他?”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想杀他。他们具体干没干,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说,我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但是我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就是我到你这儿来的原因。”
“为什么会找到我呢?”
她的脸再次微微泛红。“我到城里的两家大事务所去问了一下,他们都回绝了我。我在劳伦斯以前的罗拉代克斯名片夹中偶然发现了你的名字。我想,我要请个他曾经雇过的人,似乎颇有讽刺的味道。我在谋杀组的康·多兰那里认真了解过你的情况。”
我皱起眉头说:“这个案子就是他办的,不是吗?”
尼基点了点头。“是他办的。他说你的记忆力很好。我可不愿意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讲个没完没了的。”
“多兰怎么看?他认为你是无辜的吗?”
“我想不会。但话又说回来,我已经服完刑了,那还关他什么事?”
我审视了她片刻。她很坦率,说得也在理。劳伦斯·法伊夫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家伙。我也一直不怎么喜欢他。如果她是有罪的,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旧事重提。除了还要渡过剩余的假释期之外,她的苦难已经结束了,她与社会之间所谓的债务已经一笔勾销。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我今天晚点儿会跟你联系的,到时再答复你。”
“非常感谢。我有的是钱,花多少都无所谓。”
“法伊夫太太,重新调查以前的案子我是不会收取报酬的。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即使我们查出了谁是真凶,要想定案也相当困难。我想查阅一下过去的档案,看看情况再说。”
她从她的大皮包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档案袋。“我搜集了一些剪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把这些都留给你。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纤小、冰凉,但很有力。“请叫我尼基。”
“我会跟你联系的。”我说。
因为一个保险索赔的案子,我需要出门给一条人行道上的裂缝拍照片。在她走后,我也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驾着我的大众轿车驶上了高速公路。我喜欢让自己的车里塞满东西。这辆车上就塞满了各种文件、法律书籍以及一只公文包。包里装着我的小型自动手枪、纸盒子,还有一名客户给我的一盒机油。他被两名诈骗高手骗走了两千美元,说是帮他投资到他们所谓的石油公司中。那盒机油倒是真的,但并不是他们生产的;他们在西尔斯30W型机油上贴了新标签。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逮到这两个家伙。除了这堆垃圾之外,我还在车上塞进了一只收拾妥当的过夜行李箱,天晓得是为了防备什么不时之需。我一般不愿为那些要求我仓促行动的人提供服务;但随身带着一套睡衣、牙刷和干净的内衣,总能让我觉得安心。我想我可能有些怪癖吧。我的大众车是六八年的车型,浅米色,带有各式各样的凹痕。车的发动机早就需要检修了,可我一直没时间。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起了尼基。我已经把装满剪报的马尼拉纸档案袋扔到了汽车后座上。事实上我根本不必看这些材料。劳伦斯·法伊夫办过很多离婚案,他声名远扬,号称“法庭杀手”。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不择手段,会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优势。加州和其他许多州一样,在这里,离婚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夫妻矛盾不可调和;二是精神失常无法治愈。以前,离婚案律师和私家侦探的惯用伎俩是靠捏造通奸来提出指控,不过现在这条路行不通了。但是,财产分配和监护权——也就是金钱和孩子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劳伦斯·法伊夫能够为他的客户——绝大多数是女人——夺得这一切。在法庭之外,他同样臭名远扬,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杀手”。据说在诉讼期间,判决与最后宣判之间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曾经抚慰过无数破碎的心。
我早就发现他人狡诈,几乎没有什么幽默感,可他做人严谨,为他做事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总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还提前支付报酬。但是,很多人都非常憎恨他:他夺走了男人们的财产,又辜负了女人们的信任。他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尼基当时厄运缠身:她受到了指控、遭到了审判并被认定有罪。除了那些明显涉及杀人狂的案子之外,警方总倾向于认为谋杀罪行是由我们所知或所爱的人犯下的,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居然是正确的。当你和一家五口人坐在一起共进晚?的时候,想想这些互相递送餐盘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凶犯,这真让人不寒而栗。
第三节
如果我记得没错,在劳伦斯·法伊夫被杀当晚,他曾经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查理·斯科索尼在一起喝酒。尼基则参加了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一次聚会。她先回到家中,而劳伦斯直至午夜才回家。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接受多种过敏症的治疗。在上床之前,他吞服了日常服用的胶囊,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醒了。他恶心、呕吐,并因剧烈的胃痉挛而蜷成一团。清晨来临时,他死了。尸检和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表明,他的死因是由于吃下了被磨成粉末并放置在他所服胶囊中替代了原有药末的夹竹桃。这种伎俩并不算很高明,但的确奏效。夹竹桃在加州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灌木;事实上在法伊夫家的后院里就长着一棵。在药瓶上除了他本人的指纹之外,还发现了尼基的指纹。在她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的一些条目详细记载了她已掌握丈夫与他人通奸的事实,还记下了她深受伤害、恼怒异常,并正在考虑离婚。地方检察官非常明确地认定,要想和劳伦斯·法伊夫离婚而不承担不利后果是不可能的。他以前结过婚,又离过婚。尽管他的离婚案是由另一位律师处理的,但他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并设法在财产分配中占尽了好处。加利福尼亚州在财产分配上是很严谨的,但劳伦斯·法伊夫在金钱调配方面颇有手段;即便是五五分成,他仍然能够分到大头。看起来尼基·法伊夫似乎对此相当清楚:与其通过法律手段和丈夫脱离关系,还不如采取其他措施。
她有作案的动机,也有作案的机会。大陪审团听取了证词,提交了起诉书。她一旦出庭,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哪一方能够说服十二位公民陪审员呢?很明显,地方检察官是有备而来的。尼基聘请了来自洛杉矶的法律天才——号称“必败官司之保护神”的威尔弗雷德·布伦特耐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乎等于承认她自己有罪了。整个审判都笼罩在一种哗众取宠的氛围之中。尼基年轻漂亮,出身富贵人家。这是个小城,公众又很好奇。这场好戏是不会被错过的。
圣特雷萨位于南加利福尼亚,是一座拥有八万人口的小城。它恰好坐落于太平洋与马德雷山脉之间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是落魄富人的一处避风良港。城里的公共建筑看起来就像陈旧的西班牙式教堂,而私人住宅则像杂志中的插图一样。棕榈树上那些难看的棕色叶片被修剪掉了;在蓝灰色山冈的背景下,洁白的小船在阳光下的水中荡漾,这一切让海滨广场风景如画,完美无瑕。城内中心区大多是两到三层的建筑,白色的墙、红色的瓦,线条柔和而开阔,还带有爬满了绚丽的褐红色九重葛的棚架。即便是那些贫民居住的木结构平房也不会让人觉得邋遢。
警察局坐落于接近小城中心的一条偏僻街道上。道旁是一排粉刷成薄荷绿色的小别墅;屋墙矮矮的,蓝花楹树上垂挂着淡紫色的花朵。南加利福尼亚没有秋天,火灾便是冬天的信使。冬天常常是阴云遮蔽;火灾的季节一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泥石流。此后天气便会好转。一切又周而复始,恢复正常,就像现在五月的天气一样。
我顺路将胶卷送去冲洗,随后就来到谋杀组找多兰中尉。康·多兰已经年近六十,不修边幅:眼睛下挂着眼袋、灰色的胡楂或是胡楂般的东西、松弛臃肿的脸颊;头发梳得掠过发亮的秃顶,并抹着一层不知名的男士护发品。一眼看去,他就像是个满身雷鸟酒味、整天在桥下闲游浪荡、吐得自己满鞋污秽的家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够精明。康·多兰比一般的盗贼要聪明得多。他与杀人犯们也难分高低;大多数时候,他都能逮到他们,偶尔才会弄错一回。很少有人能骗过他,不过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只不过是工作时非常专注,记忆力好而且做事十分冷静罢了。他早知道我的来意,一言不发地示意我跟他一起走进办公室。
康·多兰所谓的办公室,在任何其他地方只配给秘书用。他不喜欢与众人隔离开来,也不在乎所谓的私人空间。他喜欢靠在向后倾的椅子里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又对周围的工作状况有所关注。他用这种方式掌握了很多信息,因而不必再靠与下属交谈来了解情况。他知道手下的探员何时回来、何时外出,也知道都有谁被抓进来审问。他还知道报告未能及时写好以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他问道,语调中没有任何要帮忙的意思。
“我想看看劳伦斯·法伊夫的档案。”
他朝着我轻轻扬起一条眉毛,说:“这不符合警局的规定。我们这儿可不是公共图书馆。”
“我又没要求把它们拿走。我只是想看一下。你以前也让我这样看过的。”
“一次而已。”
“你心里清楚,我给你提供消息可不止一次了,”我说,“这次怎么又不爽快了?”
“那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那你更用不着反对了。这根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隐私。”
他脸上带着迟钝而严肃的笑容,懒洋洋地轻轻磕着一枝铅笔。我想,他可能在享受着冷冰冰地回绝我的权力。“是她杀的,金西。整个案子就是这样。”
“是你让她跟我联系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怀疑的话,为什么还要找麻烦呢?”
“我的怀疑与劳伦斯·法伊夫无关。”他说。
“那还有什么?”
“这件案子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他语焉不详地说,“或许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既得利益。”
“‘我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
“哦,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知道多少秘密。”他说。
第四节
“我也一样,”我说,“我们何必在这儿兜圈子呢?”
他露出一丝恼怒的神情,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情感。他不是个容易被看穿的人。“你知道我对你们这类人的看法。”
“瞧,就我来说,我和你干的是同一行,”我说,“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你对其他私人侦探有什么意见,但我一直没有碍过你的事;而且我对你的工作只有尊重,别无其他。我不明白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好好合作呢?”
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紧绷的嘴角泄气地松弛下来。“你要是学会调情的话,会从我这里套出更多东西来的。”他勉
看了又看
暂无推荐
验证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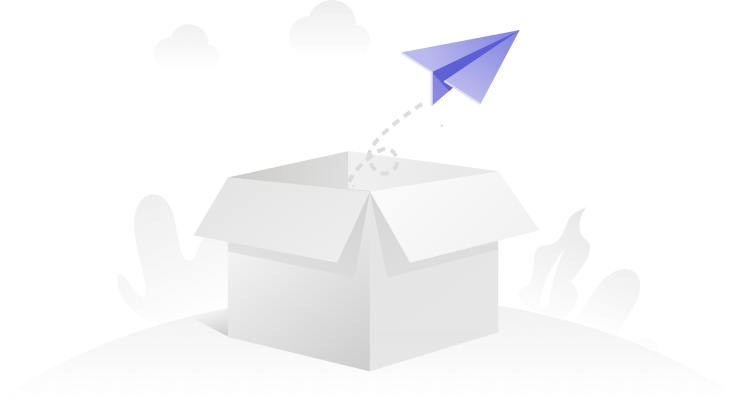
目前该文件尚无匹配的数据质量验证程序。我们将在后续版本中提供相应的验证支持,敬请谅解。

A不在现场
496.12KB
申请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