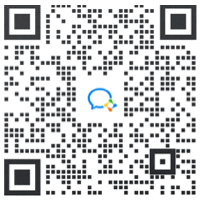目录
Content
长镜头与现实生活
时间是真实生活的依据
编剧与现实生活
每一个时代状态下的人都不一样
观点、底色与写实
一般电影是全知的观点;我则盯着主角走
我拍片子是为自己找难题
表象隐藏着暗流
对现实的关注和喜爱,文学形成了对人的看法
我比较喜欢音乐跟着影像走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1)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2)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3)
光是写实的根本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1)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2)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3)
合拍片还看不到标准
内地电影工业尚未健全,仍是计划经济
我是用影像思考,带有东方味道
杨德昌重回台湾,眼光不一样了(1)
杨德昌重回台湾,眼光不一样了(2)
别人的评论我没想看
高达是把理论放到电影去实践
国际化多是类型片,本土化则写实
创作是背对观众才开始
我的边缘人其实是正常人
电影是拍出来的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
投身电影圈
人文素养
与人相处的经验(1)
与人相处的经验(2)
与人相处的经验(3)
《尼罗河女儿》——我的城市经验
《悲情城市》——走进历史
《南国再见,南国》——回到现代
《海上花》——意外的尝试
我的能力在观察和选择上面
《千禧曼波》——发现舒淇
《咖啡时光》与《红气球》——异文化之旅(1)
《咖啡时光》与《红气球》——异文化之旅(2)
北京印象
上海风华与张爱玲
消失中的台湾电影工业
台湾纪录片
电影人青黄不接
台湾电影的未来(1)
台湾电影的未来(2)
台湾电影的未来(3)
电影教育——四所设有影视系的院校
电影学校要有制度、有好的领导
长镜头与现实生活
谈到小津,我会谈及我拍电影的形式和经验。很多人会说我的长镜头,意思就是镜头不动,然后很长。这很简单,谁都会,就是找到一个位置,把镜头放在那儿,让事情发生。但是一开始这样做是因为总感觉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专业演员,只有职业演员,他们是那种固定的表演模式,让我很没办法。我上一堂讲过,我以前在当编剧和副导演的时候,就开始用非职业演员,打架的戏就找工作人员,然后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某某的弟弟、父母,或者无意中认识的别的行业的人。在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镜头假使太靠近,他们就会紧张;假使用轨道往前推,他们会更紧张——所以没办法,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把镜头固定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如果在房间里,这个位置通常是通道,旁边有房间,可以看到窗子,可能是客厅或者所谓的饭厅。因为有窗,所以景深不错,我对密闭的空间比较没兴趣。
当你用这种方法让非职业演员开始演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不是要照剧本远远的讲话,而是要遵照房间生活的动态,这样时间就变得很重要——设定的时间到底是上午、中午还是下午。如果时间不清楚,就不能安排演员。当你有了清楚的时间,一个真实的时间观念的时候,你才有了依据,才能够判断;违背时间的状态时,我的意思是说假使一个小孩,他本应该上学,但是他回来了,而妈妈正好中午的时间在做饭,这时就会产生妈妈的反应,会问他为什么。你要安排一个状态,你就要用这样的现实时间,违背了现实时间后,你怎样安排,按照对现实时间的判断,会发生所谓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基本上就是你违背了现实时间的常理,它会发生什么。不如我刚刚说的小孩,妈妈会奇怪现在明明是上课时间,回来干吗?就冲过去问他,于是镜头就跟进去,有时声音会变成画外音,但没关系,画外音的想象空间更大。所以当我在使用这种现实的真实生活状态作为依据的时候,也就是我的电影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时间是真实生活的依据
非得要弄清楚拍每一场戏的真实时间是什么,如果不知道遵循什么,怎么依据?不能写一个:他们在打架和吵架,然后画面中他们就一直打。有一个内容就会有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房间看不见,吵架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出来,可能还有摔东西,不是直接的拍摄他们的冲突,不是一直追着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的神情走,而是非常接近我们现实生活的拍摄方法。可以设想一下,有一场戏在房间里,某个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固定在那边,接上一场戏,夫妻两个从外面回来吵架的形态。这里面就会有包括角色的惯性与细节,比如在家里爱蹲在某个地方……这些都是可以被使用的方式。所谓的戏剧性和冲突照样可以发生,而且其魅力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这样一个演变,在拍片的整个过程当中,脱逃不掉的是一定要依循现实生活的逻辑。
又有同学问及我对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也擅长长镜头拍摄手法的一些看法,与我的又有什么不同?其实如果我跟那个人很熟,通常他的电影我就不看,因为看过之后总会有一些想法,不说又忍不住,但是说了又得罪人。所以除非是传媒说得太厉害的,我才会去看,就像最近的片子一样,我去看了,但是我不会去说,直接说了就会伤人的。但是这种呢,假使能够说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我对待电影的方式和我的看法,我不会讲。但是我看电影有我独特的眼光,准得不得了,我是看到这个作者他的特点、长处、弱点以及他的限制,我会看到这个过程里面他走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会是最好的监制,真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来找我监制,都是要我挂名,我不要,我是实际要下去监制的。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监制的,我是要看这个导演的状态,看他需要什么样的搭配,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要用什么方式,或者是他没办法摆脱这种制式的规则,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堆人来了,一堆器材都配备好。但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的,而是要看什么片子,要看导演的状况。
编剧与现实生活
关于现实,有的同学问我,说“我写的剧本都是现实的生活,写得很长,但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性和张力。问题的症结在哪呢?”其实提问的同学并没有问题,而是你还没有写够,也不够认真——没有一个一个往下写,还没有形成一个看待生活的角度。因为练得还不够,所以继续写就够了。
我讲过我最早是做编剧出身的,到了后来自己做导演才开始同朱天文、吴念真一起合作。在我看来,导演一定要会编剧,不然脑子不转。虽然导演可以找人编剧,但是自己一定要懂编剧。我想东西绝对不是文字的,是画面的,是具象的、实体的,就是人跟location(场景)。你有没有看到你周遭的一些实体,比如说人、车站……特别有味道?为什么有味道?其实它是有轨迹的,有生命有洞见的。还有人,各种人都不一样,那么多人我怎么办?有时候我是看到一个人,会突然心血来潮记下他的电话,或者是我并不避讳别人介绍给我。
我在法国拍《红气球》的时候,演员候选的只有之前定下的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还有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宋芳,一个小孩西蒙,其他演员都是我去到法国后再找。律师来了,楼下那个谁谁来了,全部都好了,他们都不懂。但我认为那几个主要角色决定了之后,其他的人是根据这个主要角色而来的,我再去考虑其他人跟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影片的基调。假使楼上有吵架,要是你朋友的话,找他来演都可以,你就根据那个调整。
你看到的人、感兴趣的人又不一定是你一个年龄层次的人,那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去慢慢看。可能你看到的是他呈现的一面,可是慢慢地他就会呈现另一面,你要看清楚。当你有这个开始,你慢慢就会变得很厉害的了。所以你要下这个功夫,要认识各种人,要慢慢观察,是时间累积出来的。没有一个个体是一样的。唯一的共性是这个时代的抑制,使人们具有一个共同的部分。比如现在的风气是,大家都想很快就完成一部片子。香港金融、服务业是强项,受社会、家庭的影响,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走上这条路,而不会去走写小说的路,那比较难的,没有那个氛围。比如内地,有一个集体意识,所以他们的个人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不像西方,他们那种个人和集体意识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不会逾越,所以交往得非常舒服。但是台湾与内地,还是会介入公共事务的处理。台湾的出租车司机认为车是他的,所以他可以放烟、放香、放音乐,可以开很大声,他也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车子是他的。但问题是执照是政府给的,所以那个空间属于公共空间,就必须遵守规则,很简单的道理。以前我来香港,在电梯里面很挤,到了的时候,后面那个老外“啪”一下把我推开,我开始很愤怒,但是后来一想,活该,这是公共空间,你为什么挡人家路?台北有捷运——地下铁,也都是这样。你跟别人一起存在,你中有他,他中有你,这个就是存在。
一定要去发现你生活周遭实体,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从自己开始的,我跟吴念真、朱天文合作都是这样。我都把大概的分场写出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当然不是一次讨论完的,中间可能某一个阶段讨论,过一个阶段再讨论,等我感觉讨论得差不多了,才丢给他们再变成文字。我写的也是文字啦,只不过他们的文字功力比我厉害,所以他们去写。他们常说他们写剧本是为了工作,有人说这是为了方便,为了工作人员方便。
每一个时代状态下的人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不用小说呢?坦白讲,小说我看上的并不多,想拍的又拍不到,比如说我最想拍的几个,《合肥四姐妹》——沈从文太太张兆和的成长过程,你们有没有看过?在张兆和那个时代,那种氛围就是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她的奶妈如何处理女儿与她的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女儿都有一个“干干”,相当于保姆之类的,她的个性会影响到这个女儿,怎么负责这个家,绝对找不到这个演员,除非有人给我很多钱,我花两年时间把这些演员都找齐了,让他们这样子生活一段时间,每天排一小段,才有可能拍得出那个氛围来。因为现代人要学习以前大家族的那些细节都很难的,所以那个是没有办法改编小说。还有沈从文小说里面那个抓阄的要抓去砍头,处理好那头牛,那些人就甘心被砍头,一天砍一堆人,那些人那种脸,你去哪找?找不到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状态。现代人只能去学,但怎么学都不像。这就是我的困扰,为什么要那么挑剔呢?我拍的就是人嘛。假使拍的是事,我可以把它变成形式去表达这件事情。可我拍的是人,没办法。
为拍《聂隐娘》,我看了两个月《资治通鉴》了,感觉以前的人又直接又凶悍,非常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你归顺我,我就放过你。你是叛徒,你底下一堆人,除掉你了,那你下面的人我就都放过,然后每个人给两匹绢。半途有拿绢的就直接砍掉。我那天跟阿城再聊,这种直接不就跟“兄弟片”一样吗?兄弟片就是这样子。我以前跟李天禄聊天的时候,他比较喜欢演“三国”那个关公,他说关公就一个字——“威”,每天拿一把大刀,在马背上砍,砍人。威不威?若把他惹怒了,他那个眉毛一竖起来,不威吗?他当然威嘛,但那是练出来的。兄弟,是打出来的。有一个纪录片,讲一对相扑兄弟。那就像运动员一样,从小练的,练反射。你看他那个样子,完全像动物一样,他简直气足得不得了。拍兄弟、黑社会,不是在那边姿态怎么样,他若是那个样子他就是。比如我拍的《南国再见,南国》,我常常会在里面出现。那些人不需要什么姿态的,本身就是那样子,从小打架打到大的。所以不看那些东西(《资治通鉴》),就找不到底色。虽然不是很远,但是也有一千多年啊。在这当中,有很多东西留下来。如果要找到这些人来演,他们不是穿得漂漂亮亮就可以的,没任何意义。所以,我怎么把唐朝呈现出来,是透过我的主观、我的理解,对人的理解,然后去寻找,最后把它再次呈现。这个第二次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真实。因为你有个眼光,经历过才可能做到。
这个要张震演,打死他也演不会。演员演不好,是导演的责任,不是演员的责任。导演有什么地方没做到,害演员演不出来,导演怎么能怪演员呢?除非是好莱坞系统,演员的工资是很高的,当然要自己负责。有没有看过《迈阿密风云》里面角色的背景种种,那个导演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因为这对巩俐来说是很难的,巩俐的成长背景里面没有那种。在古巴,能够成为黑社会大佬的女朋友,实际上是干女儿,是有作为的,那这个女人还得了啊。想想看,那是多复杂的社会,多复杂的结构,她是有种气的,而且她不止一个人,她要是一帮的,才能够是那种味道。不是只是依傍在黑社会大佬旁边,假使是花瓶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她是黑帮老大没出现之前做指挥的。她凭什么指挥?这很重要,看过就会知道,可这个导演都没有给过她(巩俐)东西看啊。
观点、底色与写实
我们通常在模仿现实,再造现实。思考一场戏时,会发生一个主观的视点,就是导演自己的观点,导演会判断这样的戏和这样的情境,它的意涵,它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我习惯的观点是跟着一个主要角色,比如跟着舒淇,《最好的时光》中间那段跟着舒淇,前面那段就不是:全知,有舒淇的观点,也有张震的观点。通常在西方电影的观点是全知的,这样比较方便叙事,才会有正反两边。那通常我的电影都是盯着女主角走,就是说,所有的结构、所有的场,都不能跳开女主角,那很难办,那很现实,对不对?但那会发生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这种事在很多人的电影里都是这样使用的,基本上是客观的,全知的观点是最多的。锁定一个人的是最少的,因为限制很大,所以电影的形式就出来了,味道就不一样了,表达形态也就会不一样。比如我要拍一个张爱玲的故事,张爱玲从小就因为那个后母,最后差点死掉,后来逃出来。假使只拍她的观点,就不会去拍父亲的反应、行为,假若会拍到父亲也是因为张爱玲的行为带出来她父亲的行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假使拍好莱坞那些片子,它一定要走全知路的。比如说《神鬼认证》(The Bourne Identity),是一个失忆的杀手。开始是他漂浮在海上,被别人救起来,但他的记忆没了。男主角演了三集,第三集是英国导演拍的,他本来也是拍艺术片的,被好莱坞看中,就去拍这种片子。在那边我就感觉,他不是只跟着他,还有他对立面的一边。因为通常叙事绝对是这样,你提出观点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我对这种全知的视点,还没开始拍、没开始使用,那东西(全知视点)其实很有力量——叙事的力量,因为那样的叙事就等于是上帝,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关系,另外那个人又跟这个人有关系,最后怎么样,其实有对立两面,而且有时是不止两面,有很多面的,这样叙事上非常方便。但是我的片子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就是通常会盯着一个人,《海上花》算是一个客观的事,是全知的。像我早期的很多片子都是盯着一个角色走。我在法国拍那个片子《红气球》是盯着一个小孩和他的保姆,所以茱丽叶·比诺什的出现一定是和保姆和小孩有关才会出现,她不会单独出现。这就是看你取什么样的观点。写小说也一样,主人翁的观点。要是看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完全是那个主角女子的观点,其实这就是不一样的味道,蛮有意思的。假使说在镜头上的观点——像我的习惯就是角色眼睛看到的或者是意识里想到的,还有就是导演看到的导演想的。角色有很多,导演是一个,导演看到的、想的,结构起来,在影像的使用上其实并不难。但是我的那个叙事观点就不一样了。
一般电影是全知的观点;我则盯着主角走
就像我们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个声音“咔”——激烈的刹车声,你会回头看,但看到的不是撞车的那一刻,而是撞后的一系列状况,有人从里面出来,有人跑过来等等,可能撞到一个小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这起车祸?我会想我们的社会结构,大家开车没有概念,车要让人,第二个可能是交通的设计,我们的政府烂。这样的生活片段处处都有,我的意思是你要copy(复制)一场车祸拍,你就要理解这个状态,你可能会想背后在批判这个体制,于是就用车祸的事件放到电影里面去批判。在还原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把它弄得很残忍,小孩子很惨,拍得很惨,目的是要控诉背后的政府,表现一个直接的意义,但是这个还原的过程真实性不够。如果你反过来表现撞后的状态,表现小孩子活过来,或许这更接近真实,这个真实的意义其实大于你本来要阐述的背后的象征意义。我们在还原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毛病,你当导演当编剧在写的时候,会往设定的或者个人主观感受的这个想法上去还原,但是如果不让他活过来的话,你就只有一个狭隘的眼光。因为只要是真实的状态,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最直接的就是表面的,你就想到这点了:一场车祸,这个司机真该死,没有人会想到背后的因素是整个社会机制上的问题。懂的人安排得好,结构得好,实际上说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东西,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这样,他用的是生活中最简单的事件和元素。通常我们有个习惯,老想把这些戏剧化,冲突多一点,激烈一点,所以设计总往这边导向,而恰恰却忘了生活本身。
很多人说我的电影太平淡,没有戏剧性。其实我以前的片子是非常卖座的,卖座到一定程度,我是非常清楚的。至于争取观众的问题,这是一个鉴赏力的问题,高度的问题,我作为导演没有办法,没
Content
长镜头与现实生活
时间是真实生活的依据
编剧与现实生活
每一个时代状态下的人都不一样
观点、底色与写实
一般电影是全知的观点;我则盯着主角走
我拍片子是为自己找难题
表象隐藏着暗流
对现实的关注和喜爱,文学形成了对人的看法
我比较喜欢音乐跟着影像走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1)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2)
选演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3)
光是写实的根本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1)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2)
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3)
合拍片还看不到标准
内地电影工业尚未健全,仍是计划经济
我是用影像思考,带有东方味道
杨德昌重回台湾,眼光不一样了(1)
杨德昌重回台湾,眼光不一样了(2)
别人的评论我没想看
高达是把理论放到电影去实践
国际化多是类型片,本土化则写实
创作是背对观众才开始
我的边缘人其实是正常人
电影是拍出来的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
投身电影圈
人文素养
与人相处的经验(1)
与人相处的经验(2)
与人相处的经验(3)
《尼罗河女儿》——我的城市经验
《悲情城市》——走进历史
《南国再见,南国》——回到现代
《海上花》——意外的尝试
我的能力在观察和选择上面
《千禧曼波》——发现舒淇
《咖啡时光》与《红气球》——异文化之旅(1)
《咖啡时光》与《红气球》——异文化之旅(2)
北京印象
上海风华与张爱玲
消失中的台湾电影工业
台湾纪录片
电影人青黄不接
台湾电影的未来(1)
台湾电影的未来(2)
台湾电影的未来(3)
电影教育——四所设有影视系的院校
电影学校要有制度、有好的领导
长镜头与现实生活
谈到小津,我会谈及我拍电影的形式和经验。很多人会说我的长镜头,意思就是镜头不动,然后很长。这很简单,谁都会,就是找到一个位置,把镜头放在那儿,让事情发生。但是一开始这样做是因为总感觉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专业演员,只有职业演员,他们是那种固定的表演模式,让我很没办法。我上一堂讲过,我以前在当编剧和副导演的时候,就开始用非职业演员,打架的戏就找工作人员,然后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某某的弟弟、父母,或者无意中认识的别的行业的人。在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镜头假使太靠近,他们就会紧张;假使用轨道往前推,他们会更紧张——所以没办法,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把镜头固定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如果在房间里,这个位置通常是通道,旁边有房间,可以看到窗子,可能是客厅或者所谓的饭厅。因为有窗,所以景深不错,我对密闭的空间比较没兴趣。
当你用这种方法让非职业演员开始演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不是要照剧本远远的讲话,而是要遵照房间生活的动态,这样时间就变得很重要——设定的时间到底是上午、中午还是下午。如果时间不清楚,就不能安排演员。当你有了清楚的时间,一个真实的时间观念的时候,你才有了依据,才能够判断;违背时间的状态时,我的意思是说假使一个小孩,他本应该上学,但是他回来了,而妈妈正好中午的时间在做饭,这时就会产生妈妈的反应,会问他为什么。你要安排一个状态,你就要用这样的现实时间,违背了现实时间后,你怎样安排,按照对现实时间的判断,会发生所谓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基本上就是你违背了现实时间的常理,它会发生什么。不如我刚刚说的小孩,妈妈会奇怪现在明明是上课时间,回来干吗?就冲过去问他,于是镜头就跟进去,有时声音会变成画外音,但没关系,画外音的想象空间更大。所以当我在使用这种现实的真实生活状态作为依据的时候,也就是我的电影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时间是真实生活的依据
非得要弄清楚拍每一场戏的真实时间是什么,如果不知道遵循什么,怎么依据?不能写一个:他们在打架和吵架,然后画面中他们就一直打。有一个内容就会有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房间看不见,吵架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出来,可能还有摔东西,不是直接的拍摄他们的冲突,不是一直追着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的神情走,而是非常接近我们现实生活的拍摄方法。可以设想一下,有一场戏在房间里,某个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固定在那边,接上一场戏,夫妻两个从外面回来吵架的形态。这里面就会有包括角色的惯性与细节,比如在家里爱蹲在某个地方……这些都是可以被使用的方式。所谓的戏剧性和冲突照样可以发生,而且其魅力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这样一个演变,在拍片的整个过程当中,脱逃不掉的是一定要依循现实生活的逻辑。
又有同学问及我对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也擅长长镜头拍摄手法的一些看法,与我的又有什么不同?其实如果我跟那个人很熟,通常他的电影我就不看,因为看过之后总会有一些想法,不说又忍不住,但是说了又得罪人。所以除非是传媒说得太厉害的,我才会去看,就像最近的片子一样,我去看了,但是我不会去说,直接说了就会伤人的。但是这种呢,假使能够说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我对待电影的方式和我的看法,我不会讲。但是我看电影有我独特的眼光,准得不得了,我是看到这个作者他的特点、长处、弱点以及他的限制,我会看到这个过程里面他走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会是最好的监制,真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来找我监制,都是要我挂名,我不要,我是实际要下去监制的。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监制的,我是要看这个导演的状态,看他需要什么样的搭配,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要用什么方式,或者是他没办法摆脱这种制式的规则,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堆人来了,一堆器材都配备好。但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的,而是要看什么片子,要看导演的状况。
编剧与现实生活
关于现实,有的同学问我,说“我写的剧本都是现实的生活,写得很长,但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性和张力。问题的症结在哪呢?”其实提问的同学并没有问题,而是你还没有写够,也不够认真——没有一个一个往下写,还没有形成一个看待生活的角度。因为练得还不够,所以继续写就够了。
我讲过我最早是做编剧出身的,到了后来自己做导演才开始同朱天文、吴念真一起合作。在我看来,导演一定要会编剧,不然脑子不转。虽然导演可以找人编剧,但是自己一定要懂编剧。我想东西绝对不是文字的,是画面的,是具象的、实体的,就是人跟location(场景)。你有没有看到你周遭的一些实体,比如说人、车站……特别有味道?为什么有味道?其实它是有轨迹的,有生命有洞见的。还有人,各种人都不一样,那么多人我怎么办?有时候我是看到一个人,会突然心血来潮记下他的电话,或者是我并不避讳别人介绍给我。
我在法国拍《红气球》的时候,演员候选的只有之前定下的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还有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宋芳,一个小孩西蒙,其他演员都是我去到法国后再找。律师来了,楼下那个谁谁来了,全部都好了,他们都不懂。但我认为那几个主要角色决定了之后,其他的人是根据这个主要角色而来的,我再去考虑其他人跟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影片的基调。假使楼上有吵架,要是你朋友的话,找他来演都可以,你就根据那个调整。
你看到的人、感兴趣的人又不一定是你一个年龄层次的人,那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去慢慢看。可能你看到的是他呈现的一面,可是慢慢地他就会呈现另一面,你要看清楚。当你有这个开始,你慢慢就会变得很厉害的了。所以你要下这个功夫,要认识各种人,要慢慢观察,是时间累积出来的。没有一个个体是一样的。唯一的共性是这个时代的抑制,使人们具有一个共同的部分。比如现在的风气是,大家都想很快就完成一部片子。香港金融、服务业是强项,受社会、家庭的影响,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走上这条路,而不会去走写小说的路,那比较难的,没有那个氛围。比如内地,有一个集体意识,所以他们的个人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不像西方,他们那种个人和集体意识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不会逾越,所以交往得非常舒服。但是台湾与内地,还是会介入公共事务的处理。台湾的出租车司机认为车是他的,所以他可以放烟、放香、放音乐,可以开很大声,他也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车子是他的。但问题是执照是政府给的,所以那个空间属于公共空间,就必须遵守规则,很简单的道理。以前我来香港,在电梯里面很挤,到了的时候,后面那个老外“啪”一下把我推开,我开始很愤怒,但是后来一想,活该,这是公共空间,你为什么挡人家路?台北有捷运——地下铁,也都是这样。你跟别人一起存在,你中有他,他中有你,这个就是存在。
一定要去发现你生活周遭实体,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从自己开始的,我跟吴念真、朱天文合作都是这样。我都把大概的分场写出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当然不是一次讨论完的,中间可能某一个阶段讨论,过一个阶段再讨论,等我感觉讨论得差不多了,才丢给他们再变成文字。我写的也是文字啦,只不过他们的文字功力比我厉害,所以他们去写。他们常说他们写剧本是为了工作,有人说这是为了方便,为了工作人员方便。
每一个时代状态下的人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不用小说呢?坦白讲,小说我看上的并不多,想拍的又拍不到,比如说我最想拍的几个,《合肥四姐妹》——沈从文太太张兆和的成长过程,你们有没有看过?在张兆和那个时代,那种氛围就是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她的奶妈如何处理女儿与她的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女儿都有一个“干干”,相当于保姆之类的,她的个性会影响到这个女儿,怎么负责这个家,绝对找不到这个演员,除非有人给我很多钱,我花两年时间把这些演员都找齐了,让他们这样子生活一段时间,每天排一小段,才有可能拍得出那个氛围来。因为现代人要学习以前大家族的那些细节都很难的,所以那个是没有办法改编小说。还有沈从文小说里面那个抓阄的要抓去砍头,处理好那头牛,那些人就甘心被砍头,一天砍一堆人,那些人那种脸,你去哪找?找不到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状态。现代人只能去学,但怎么学都不像。这就是我的困扰,为什么要那么挑剔呢?我拍的就是人嘛。假使拍的是事,我可以把它变成形式去表达这件事情。可我拍的是人,没办法。
为拍《聂隐娘》,我看了两个月《资治通鉴》了,感觉以前的人又直接又凶悍,非常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你归顺我,我就放过你。你是叛徒,你底下一堆人,除掉你了,那你下面的人我就都放过,然后每个人给两匹绢。半途有拿绢的就直接砍掉。我那天跟阿城再聊,这种直接不就跟“兄弟片”一样吗?兄弟片就是这样子。我以前跟李天禄聊天的时候,他比较喜欢演“三国”那个关公,他说关公就一个字——“威”,每天拿一把大刀,在马背上砍,砍人。威不威?若把他惹怒了,他那个眉毛一竖起来,不威吗?他当然威嘛,但那是练出来的。兄弟,是打出来的。有一个纪录片,讲一对相扑兄弟。那就像运动员一样,从小练的,练反射。你看他那个样子,完全像动物一样,他简直气足得不得了。拍兄弟、黑社会,不是在那边姿态怎么样,他若是那个样子他就是。比如我拍的《南国再见,南国》,我常常会在里面出现。那些人不需要什么姿态的,本身就是那样子,从小打架打到大的。所以不看那些东西(《资治通鉴》),就找不到底色。虽然不是很远,但是也有一千多年啊。在这当中,有很多东西留下来。如果要找到这些人来演,他们不是穿得漂漂亮亮就可以的,没任何意义。所以,我怎么把唐朝呈现出来,是透过我的主观、我的理解,对人的理解,然后去寻找,最后把它再次呈现。这个第二次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真实。因为你有个眼光,经历过才可能做到。
这个要张震演,打死他也演不会。演员演不好,是导演的责任,不是演员的责任。导演有什么地方没做到,害演员演不出来,导演怎么能怪演员呢?除非是好莱坞系统,演员的工资是很高的,当然要自己负责。有没有看过《迈阿密风云》里面角色的背景种种,那个导演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因为这对巩俐来说是很难的,巩俐的成长背景里面没有那种。在古巴,能够成为黑社会大佬的女朋友,实际上是干女儿,是有作为的,那这个女人还得了啊。想想看,那是多复杂的社会,多复杂的结构,她是有种气的,而且她不止一个人,她要是一帮的,才能够是那种味道。不是只是依傍在黑社会大佬旁边,假使是花瓶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她是黑帮老大没出现之前做指挥的。她凭什么指挥?这很重要,看过就会知道,可这个导演都没有给过她(巩俐)东西看啊。
观点、底色与写实
我们通常在模仿现实,再造现实。思考一场戏时,会发生一个主观的视点,就是导演自己的观点,导演会判断这样的戏和这样的情境,它的意涵,它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我习惯的观点是跟着一个主要角色,比如跟着舒淇,《最好的时光》中间那段跟着舒淇,前面那段就不是:全知,有舒淇的观点,也有张震的观点。通常在西方电影的观点是全知的,这样比较方便叙事,才会有正反两边。那通常我的电影都是盯着女主角走,就是说,所有的结构、所有的场,都不能跳开女主角,那很难办,那很现实,对不对?但那会发生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这种事在很多人的电影里都是这样使用的,基本上是客观的,全知的观点是最多的。锁定一个人的是最少的,因为限制很大,所以电影的形式就出来了,味道就不一样了,表达形态也就会不一样。比如我要拍一个张爱玲的故事,张爱玲从小就因为那个后母,最后差点死掉,后来逃出来。假使只拍她的观点,就不会去拍父亲的反应、行为,假若会拍到父亲也是因为张爱玲的行为带出来她父亲的行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假使拍好莱坞那些片子,它一定要走全知路的。比如说《神鬼认证》(The Bourne Identity),是一个失忆的杀手。开始是他漂浮在海上,被别人救起来,但他的记忆没了。男主角演了三集,第三集是英国导演拍的,他本来也是拍艺术片的,被好莱坞看中,就去拍这种片子。在那边我就感觉,他不是只跟着他,还有他对立面的一边。因为通常叙事绝对是这样,你提出观点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我对这种全知的视点,还没开始拍、没开始使用,那东西(全知视点)其实很有力量——叙事的力量,因为那样的叙事就等于是上帝,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关系,另外那个人又跟这个人有关系,最后怎么样,其实有对立两面,而且有时是不止两面,有很多面的,这样叙事上非常方便。但是我的片子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就是通常会盯着一个人,《海上花》算是一个客观的事,是全知的。像我早期的很多片子都是盯着一个角色走。我在法国拍那个片子《红气球》是盯着一个小孩和他的保姆,所以茱丽叶·比诺什的出现一定是和保姆和小孩有关才会出现,她不会单独出现。这就是看你取什么样的观点。写小说也一样,主人翁的观点。要是看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完全是那个主角女子的观点,其实这就是不一样的味道,蛮有意思的。假使说在镜头上的观点——像我的习惯就是角色眼睛看到的或者是意识里想到的,还有就是导演看到的导演想的。角色有很多,导演是一个,导演看到的、想的,结构起来,在影像的使用上其实并不难。但是我的那个叙事观点就不一样了。
一般电影是全知的观点;我则盯着主角走
就像我们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个声音“咔”——激烈的刹车声,你会回头看,但看到的不是撞车的那一刻,而是撞后的一系列状况,有人从里面出来,有人跑过来等等,可能撞到一个小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这起车祸?我会想我们的社会结构,大家开车没有概念,车要让人,第二个可能是交通的设计,我们的政府烂。这样的生活片段处处都有,我的意思是你要copy(复制)一场车祸拍,你就要理解这个状态,你可能会想背后在批判这个体制,于是就用车祸的事件放到电影里面去批判。在还原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把它弄得很残忍,小孩子很惨,拍得很惨,目的是要控诉背后的政府,表现一个直接的意义,但是这个还原的过程真实性不够。如果你反过来表现撞后的状态,表现小孩子活过来,或许这更接近真实,这个真实的意义其实大于你本来要阐述的背后的象征意义。我们在还原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毛病,你当导演当编剧在写的时候,会往设定的或者个人主观感受的这个想法上去还原,但是如果不让他活过来的话,你就只有一个狭隘的眼光。因为只要是真实的状态,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最直接的就是表面的,你就想到这点了:一场车祸,这个司机真该死,没有人会想到背后的因素是整个社会机制上的问题。懂的人安排得好,结构得好,实际上说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东西,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这样,他用的是生活中最简单的事件和元素。通常我们有个习惯,老想把这些戏剧化,冲突多一点,激烈一点,所以设计总往这边导向,而恰恰却忘了生活本身。
很多人说我的电影太平淡,没有戏剧性。其实我以前的片子是非常卖座的,卖座到一定程度,我是非常清楚的。至于争取观众的问题,这是一个鉴赏力的问题,高度的问题,我作为导演没有办法,没
看了又看
暂无推荐
验证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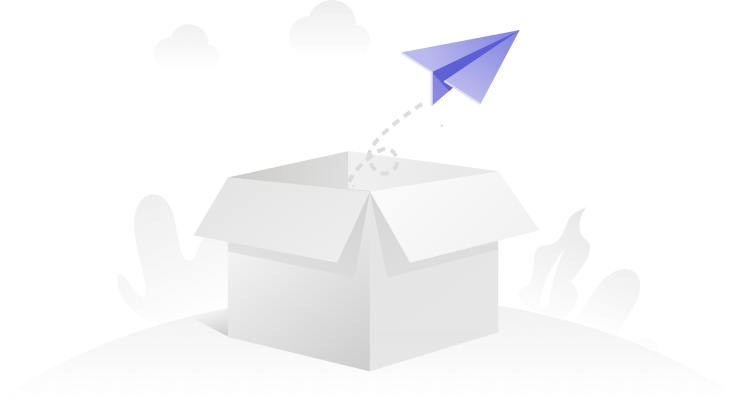
目前该文件尚无匹配的数据质量验证程序。我们将在后续版本中提供相应的验证支持,敬请谅解。

侯孝贤电影讲座
456.8KB
申请报告